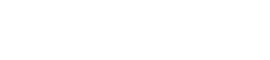第九十一回
避春雨巧逢袁太监 走内线参倒严世蕃
词曰:
郊原外,雨涓涓,杯酒与他同醉,论权奸。
一疏已有内线,欣逢术士周旋,严饬刑曹究此案,万人欢。
——右调《春光好》。
前回言袁不邪回玉屋洞,火龙颁法旨,于冰赴九功山,这话不表。且说邹应龙自林润出巡江南后,日夜留心严嵩父子款件,虽皆件件的确,只是不敢下手。此年他胞叔邹雯来下会试场,因不中,急欲回家。应龙凑了些盘费,亲自送出彰义门外。
见绿柳已舒新眉,残桃犹有余笑。蒙茸细草,步步衬着马蹄,鸟语禽声,与绿水潺湲之声相应。遥望西山一带,流青积翠,如在眼前。因贪看春色,直送了二十余里。忽然落下雨来,起初点点滴滴,时停时止,次后竟大下起来。又没有带着雨具,衣襟已有湿痕。猛见前面,坐北朝南,有一处园林,内中隐隐露出楼阁。随吩咐家人,策马急趋。
到了门前,守门的问道:“做什么?”
家人们道:“我家老爷姓邹,现任御史。因送亲遇雨,欲到里面暂避一刻。”
守门人道:“请老爷暂在门内略等等,我去问声主人,再来回覆。”
少刻,守门人跑出道:“我家老爷相请,已迎接出来了。”
应龙下马,随那人走入第一层园门。只见一个太监,后跟着五六个家丁,七八个小内官,都站在第二层门内等候。见应龙到了面前,方下台阶来。举手笑说道:“老先是贵客,难得到我们这儿来。”
应龙也举手道:“因一时遇雨,无可回避处,故敢造次趋谒。”
那太监又笑道:“你若不是下雨,做梦儿也不来。”
说罢,拉着应龙的手儿,并行入去。到一敞厅内,叙礼坐下。
太监道:“方才守门的小厮说老先姓邹,现做御史,不晓得尊讳叫什么?”
应龙道:“小弟叫邹应龙。”
那太监道:“这到和上科状元是一个样儿的名字,难得。”
应龙笑道:“上科徼幸,就是小弟。”
那太监道:“呵呀!你是个状元御史,要算普天下第一个文章头儿,与别的官儿不同,我要分外的敬你了。快请到里面去坐。这个地方儿平常,不是教状元坐的去处。我还要请教你的文墨和你的学问。”
应龙笑道:“若是这样,小弟只在此处坐罢,被老公公考较倒了,那时反难藏拙。”
那太监大笑道:“好约薄话儿,笑话我们内官不识字,你自试试瞧。”
于是又拉了应龙的手儿,过了敞厅,循着花墙北走。
又入了一层门儿,放眼一看,见前后高高下下,有无数的楼阁台榭,中间郁郁苍苍,树木参差,假山鱼池,分列左右,到也修盖的富丽。又领应龙到一亭子内,见四面垂着竹帘,亭子周围,都是牡丹。也有正开的,也有开败的,一朵朵含芳吐卉,若花茵锦帐一般,无愧国色天香之誉。再看那雨,已下的小了,两人就坐,左右献上茶来。
应龙道:“小弟还没有请教老公公高姓大讳,并在内庭所执何事?”
那太监道:“我姓袁,名字叫天喜。”
应龙道:“可是元亨利贞的元字么了”
太监道:“不是了,我这姓,和那表兄、表弟的表字差不多。”
应龙笑道:“小弟明白了,尊姓果然像个表字。”
袁太监拍手大笑道:“何如?连你也说像了。我如今现掌上衣监事,这几日才将夏季衣服交入去,又要于办秋季的衣服。昨日趁闲空儿出来走走。”
应龙将他出入禁掖、日伴君王的事,着实誉扬了几句。又将他的花园也极口道好。
袁太监大乐,向众小内官道:“这邹老爷是大黑儿疤的状元出身,不是顽儿的。”
他嘴里从不夸奖人,人若是教他夸奖了,这个人一万年也不错。众小内官和家丁们齐声答应道:“是,是!”
袁太监又向众人道:“我们坐了这半天,也不弄点吃的东西,都挤在这里听说话儿。”
应龙道:“此刻雨小了,小弟别过罢。”
袁太监恼了,道:“这都是把人当亡八羔子待哩!难道我们做内官的,就陪状元吃不得一杯酒么!就立刻要告辞。你不来不怎么!”
应龙见袁太监恼了,忙笑说道:“小弟为初次相会,实不好讨扰。今既承厚爱,小弟吃个烂醉去,何如?”
袁太监又笑了,说道:“归根儿这一句,才像个状元的话。”
须臾,盘盛异品,酒泛金波,山珍海错,摆满春台。食物亦多外面买不出来的东西。应龙见袁太监人爽直,也不作客,杯到即干。吃到半酣时分,应龙道:“小弟躬逢盛景,兼对名花,此时诗兴发作,意欲在这外面粉墙上写诗一首,只恐俚句粗俗,有污清目。”
袁太监道:“你是中过状元的人,做诗还论什么里外?里做也是好的,外做也是好的,但是诗与我不合脾胃,到是好曲儿写几个,我闲了出来,看的唱唱,也是一乐。若说做诗,我们管奏疏的乔老哥,他还是个名公。”
应龙道:“可是乔讳承泽的么?”
袁太监道:“这又奇了,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
应龙道:“去岁秋间,圣上将他做的诗三十余首发到翰林院,着众词臣公看。也还难为他,竟做的明白。”
袁太监笑道:“他才止是个明白,不该我说,翰林院里除了你,还没有第二个人做的过他哩。”
应龙笑道:“我也做不过他。”
袁太监道:“你到不必谦着说,他实利害的多着哩。我们见他拿起笔来,写小字儿还略费点功夫,写大字,只用几抹子,就停当了。去年八月里,他到我这儿来,也要在我墙上写诗,我紧拉着,我就写了半墙。他去了,我叫了个泥匠把他的字刮吊,又从新粉了个雪白。后来他知道了,他到说我是个俗品。你公道说罢,这墙还是白白儿的好,还是涂黑了好哩?”
应龙道:“自然是白的好。”
袁太监道:“既然知道白的好,你还为什么要写?”
应龙笑道:“我当你不爱白的。”
自此将做诗的话,再不题了。两人只是吃酒。袁太监又叫过几个小内监来,唱《寄生草》、《粉红莲》、《凤阳歌》,唱了一会,向应龙道:“这个地方儿吃酒低,我们到高处去罢。”
应龙道:“高处吃酒,自然又好是低处了。”
袁太监大乐,吩咐家人移酒到披云楼上。
两人行到楼上坐下,将四面窗隔打开。只见青山叠翠,绿柳垂金,远近花枝,红白相映,大是豁目赏心。两人复行畅饮,又听了会曲儿。应龙见袁太监有酒了,便低低说道:“小弟有心腹话要请教,祈将尊纪们暂时退去。”
袁太监问众人道:“邹老爷有体己话儿告诉我,你们把酒留两壶在桌上,我们自己斟着吃。打发邹老爷的人吃饭。不醉了,我不依。”
众人答应,一齐下楼去了。应龙道:“老公公日在圣上左右,定知圣心。年来诸大臣内,圣上心中,到的宠爱那个?”
袁太监道:“宠爱的内外大臣,也有十来个,总不如吏部尚书徐阶第一。你听着罢,就要做宰相哩。”
应龙道:“比严中堂还在上么?”
袁太监道:“你说的是严嵩么?”
应龙道:“正是。”
袁太监道:“那老小妇的,走了背运了。”
应龙忙问道:“我见圣上始终如一,笼眷与前无异,怎么说他走了背运?”
袁太监道:“你们外边的官儿,那里知道内里的事?二年以前,这老头子还是站着的皇帝。不知怎么,从去年至今,青词也做的不好了。批发的本章拟奏上去,都不如圣意。启奏的事,万岁爷未尝不准他的,只是心上不舒服。”
应龙道:“老公公何以知道这般详细?”
袁太监道:“我在上衣监见万岁爷的时候少,一月不过两三次。司理监赵老哥和奏疏上的乔老哥,他们两个是日夜不离的。万岁爷脸上略有点喜怒,他们就可以猜个八九分儿。是为什么事体,一个爱严嵩不爱,有什么难测度处。”
应龙以手加额道:“此社稷之福也!”
袁太监道:“你说是谁的福?社稷是个什么人?”
应龙道:“我没有什么福不福。”
袁太监拂然道:“你这人就难相与了。你今儿个和我一会,咱们从今日就是好哥儿,好弟兄,好朋友。我的爹妈,就是你的父母,我的侄儿子们,就是你的儿女。有了话,你也不要瞒我,我也不要瞒你。你方才来来回回盘问爱谁不爱谁,必定有个意思。又把严老头子紧着问,你到的是心上疼他?还是恼他哩?你只管告诉我,我替你拿主意。你要怕我走了话,我到来生来世,还做个老公,教人家割了去。这个誓儿,对不过你么?”
应龙道:“老公公出入内庭,品端行方,断断不是走话的人。弟因严嵩父子屠毒万姓,杀害忠良,贪赃卖官,权倾中外。久欲参他一本,诚恐学了前人,徒死无益国家。适听公公说他圣眷渐哀,谅非虚语。小弟志愿已决,今晚回去,定连夜草成奏疏,上达宸听。事之成败,我与老贼各听天命罢了。”
袁太监把桌子一拍,道:“好,好!你听我告诉你:你前几年参他,不但参不倒,且有祸患。若再迟几年参他,他将万岁爷又奉承喜欢了,可惜就失了机会。如今不迟不早,正是分儿。你做这件事,不但成就了你的声名,还替我报了仇恨,正是一举两得。”
应龙道:“老公公与他毫无交涉,怎么说‘仇恨’二字?”
袁太监道:“说起来,我就恼死。我们祖籍是河间府人。我自入宫后这二十多年,也弄下几个钱儿。我的父母也死了,只有个同胞的老哥哥,和几个侄儿子,在珠宝市儿,买了两处大铺房,费了四千二百来两的银子。只讨了半年房钱,不意他家有个总管,叫什么阎七,他硬出来做原业主,只给了我哥哥二千两银子,就把两处铺房都赎了去。我哥哥不敢惹他,我又怕弄出是非来,教万岁爷说我们有钱。赔了二千二百多两本儿,教他克了去。你说气也不气?分明他还知道是我们内官的房子,若是平常人,休说找二千,连一千还未必找给。你今日要参他,我心上先就乐起。还有个诀窍,我说给你:你的参本,别要在通政司挂号,那老奴才耳目众多,一露风声,你的本章白搁在那儿,他就着人先参了你。当日那赵文华,不知和他做了这们多少次。我们内里都知道,谁肯在万岁爷前翻这个舌头?今日四月初二日,也功夫忒促急,你定到四月初四日,早饭后,亲到内阁,我教管奏疏的乔老哥在内阁等你。你暗暗的递与他就是了。我们哥儿两,相交的最厚,年年总要送他几套衣服穿。”
应龙道:“这乔公公,虽素日闻名,只是认识不得他。万一交错了,关系非浅。”
袁太监道:“他有什么难认?一脸麻子,长条身材,穿着蟒衣玉带。且他常到内阁,和中堂们说话儿。别的内官,没有旨意,谁敢到内阁里去?”
应龙道:“假若圣上追究不由通政司挂号,该怎么处?”
袁太监道:“你好罗嗦呀!这样个胆儿,就想参人!你不由通政司挂号,是你的不是,他私自收你的本章,替你传送,难道他不担干系么?只因他有那个武艺儿,他才敢收你的本章哩。我想了一会,你且不要参严老头子。他受恩多年,此时他就要算国之元老。你一个上科新进的小臣,虽说是言官,你参的他轻了,白拉倒,惹的他害你。参的语言过重,万岁爷看见许多款件,无数的要迹。他闹了好些年,竟毫无觉查,脸上也对不过诸王大臣和普天下的百姓,只怕你也讨不了公道。依我的主见,你莫妙于只参他的儿子严世蕃,和他家人阎七等。搬倒小的儿,大的不怕他不随着倒。这就替万岁爷留下处分他父子的地步了。比如一窝燕儿,你把小燕儿都弄死,那大燕儿,还想安然住着么?”
应龙连忙站起,叩谢道:“老公公明见,匪夷所思,真令人佩服感激之至!小弟就如此行。此时雨已不下多时了,小弟告辞罢。”
袁太监还礼后,说道:“好容易知己哥儿们遇着,你不如在这儿住一宿,明日我和你一同进城。”
应龙向袁太监耳边说道:“我回去要做参本,等我参倒严嵩父子,你有功夫,我就来陪你,只用你着人叫我一声。”
袁太监大乐,道:“这们的敢只好。还有句话,我说给你:若见了乔老哥,叫不得他老公公。这老公公是老婆婆的对面儿,不是什么高贵称呼。”
应龙连连作揖,道:“小弟山野,整叫了你一天老公公,该死,该死!”
袁太监亦急忙还揖道:“你好多心呀!你当我恼你么?我要恼你,我就不说了。你叫我老公公,我知道你是心上敬我。我只怕你得罪了乔老哥。”
应龙又作揖道:“你还不快指教我,到的该称呼什么才好?”
袁太监笑道:“你的礼忒多,到底还和我是两个人。你听我教给你:比如他要叫你邹先儿,这和你们叫老公公一样,你称呼他老司长。他叫你邹老先生,这是去了儿字加敬了,你称呼他乔老爷。他若叫你邹老爷,你称呼他乔大人。他是衣蟒腰玉的老公,比我们不同。不但你,严老头子到是个宰相,还叫他大人不绝口。这是本朝开国元勋,我们刚丙老爷,给我们挣下的这们点脸面儿。你既要做打老虎的事,必须处处让他占个上分儿,就得了窍了。我说的是不是?”
应龙道:“小弟心上,终身感激不尽。”
袁太监道:“你放心做去罢,我内里替你托几个人,也是一臂之力。”
应龙道:“更感厚情不尽。”
两人携手出园,叮咛后会。应龙骑在马上,袁太监道:“邹老爷,戏里头有两句:‘眼观捷旌旗,耳听好消息。”
应龙在马上伏首道:“仰赖福庇,定必成功!”
袁太监只等的看不见应龙,方回园内,向众小内官道:“这邹状元到还没有那种纱帽气,心上待人也真。他就在这几天要做人不敢做的事,竟是个好汉子。我明日定恳司理监赵老爷和乔老爷暗中帮帮他。”
说着,入里面去了。
再说邹应龙回到家中,越想那袁太监的话越有道理。想了半夜,然后起稿。上写道:
福建道监察御史臣邹应龙,一本为参奏事。窃以工部侍郎严世蕃,凭藉父权,专利无厌,私擅封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竞趋,要价转巨。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三百金得知州。夫司属郡吏,赂以千万,则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纪极!平时交通赃贿,为之居间者,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阎年,幕客中书罗龙文为甚。年尤桀黠,仕宦人无耻者,至呼为萼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节,辄献万金为寿。臧获富侈若此,是主人当何如!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恃势鲸吞,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乡里可知。嵩妻病疫,圣上殊恩,念嵩年老,特留世蕃侍养,令鹄扶榇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灭绝。至鹄之无知,则以祖母丧为奇货,所至驿站,要索百端。诸司承命,郡邑为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惊。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内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豁壑,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也!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宜疾放归田,用清政本。天下幸甚!臣应龙无任惶恐待命之至。谨奏。
写完,看了几遍,至次日,用楷书写清。到初四日,一早入朝。直候到饭时。在内阁,见一蟒衣太监,面麻身长,倚着门儿站立。又见有许多大员在那里强着和他说话。应龙心里说道:“这必是乔太监无疑。”
急走至面前,先与他深深一揖。
那太监还了半揖,道:“老先少会的狠,贵姓哩?”
应龙道:“姓邹。”
那太监道:“可是上科状元,如今做御史的么?”
应龙道:“正是。”
太监笑道:“前日和袁敝友吃酒好乐,他是个俗物,把你的诗兴都阻了。我姓乔,正要寻你问句话儿,你跟我来。”
将应龙引到西边一板屋墙下,说道:“你的奏疏有了么?”
应龙连忙从袖中取出,递与乔太监道:“统望大人照拂。”
太监接来,也向袖内一塞,道:“你这事,系袁敝友再三相托。有点缝儿,我就替你用力。”
应龙连连作揖。乔太监拉住道:“你不要多礼,事成之后,我有几首诗要发刻,一则求你改削。二则还要藉重你的大名做篇序文。你却不可过河拆桥。”
应龙道:“正要捧读大人珠玉。至于叙文,欲用贱名,越发叨光不尽了。小弟妹丈林润,系新科榜眼。他虽出巡江南,弟亦可代做序文,并书舍妹丈名讳,可使得么?”
乔太监乐的拍手大笑道:“我的诗原无佳句,得二位鼎甲一誉扬,定必长安纸贵,价重南京矣。但不知令亲林润可就是参赵文华的那个少年翰林么?”
应龙道:“正是他。”
乔太监乐的手舞足蹈道:“得他一篇序文,我这品行学问,高到那儿去了。你要知道,他昔日参赵文华,就是参严中堂。你今日又参他,怎么你郎舅们都是铁汉子。我再说给你,万岁爷和严中堂是前生前世百世奇缘,想要弄倒他,难而又难。也罢了,我再替你内里托两个人罢。”
应龙又谢。乔太监道:“我们别了罢,改日还要在袁敝友园中领教。你这本,或今日午后,至迟明早,定有旨意。”
应龙别了出来,也无心上衙门,回家坐候吉凶。
乔太监将应龙奏疏带到宫内,同六部本章放在一处,却放在第二个本章下面。等的明帝到批发本章时,乔太监放在桌上。
明帝看到应龙参严世蕃并阎年等,心下大为诧异。问乔太监道:“怎么参本和六部现行事件放在一处?”
乔太监跪奏道:“此系御史邹应龙亲到宫门,未经通政司挂号,因此放在六部现行事件内。”
明帝也就不追问了。又往下细看,心里说道:“严世蕃等倚仗严嵩,竟敢如此作恶,严嵩慢无约束,是何道理?”又想道:“世蕃系大学士之子,言官参他,不得不放重些。大要虚多实少。”
正欲想算批发,猛见方士蓝道行站在下面。明帝此时深宠信他,因他善会扶鸾。说道:“朕有一事不决,藉乩明示。”
随即驾到鸾房。蓝道行问道:“陛下所问何事?”
明帝道:“朕心默祝,你只管照鸾词书写出来就是。”
乔太监便使了个眼色。蓝道行前受袁太监嘱托,午间又受乔太监和赵太监嘱托,适间问应龙参本话,他又是听见的。此刻乔太监又递眼色,心里早已透亮。少刻,乩笔在沙盘中乱动,他却不看写的是什么。
随用自己的意见写出几句话来道:“严嵩主持国柄,屡行杀害忠良。子世蕃等贪赂无已,宜速加显戮,快天下臣民之心。”
明帝看了,心上大是钦服。随即回原看本处,将应龙本章批道:“览邹应龙参奏,朕心深为骇异。严世蕃等俱着革职,拿送刑部。其种种不法,着三法司将本内有名人犯,一并严审,定拟具奏。邹应龙即着升授通政司政卿。钦此!”
这道旨意一下,京师震动,将应龙此本家传户诵。都乱讲先时有许多不怕死的官儿,不但未将严嵩父子动着分毫,并连他的党羽也没弄倒半个。谁想教个新进书生,到成了大功。真是出人意外。只十数日,便遍传天下皆知。
正是:
避雨无心逢内宦,片言杯酒杀奸雄,
忠臣义士徒拚命,一纸功成属应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