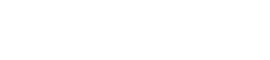第七十回
听危言断绝红尘念 寻旧梦永结道中缘
词曰:
园亭破碎潦倒,好梦儿去了。追往惜来,无那柔肠搅。
回思事实幻杳,一会面人皆先觉。寻访原迹,回头惟愿早。
——右调《伤情怨》。
话说温如玉在那破花园门外睹景徘徊,回想他的功名首尾,并夫妻恩爱,子孙缠绵,三十余年出将人相事业,不过半日功夫,统归乌有,依旧是个落魄子弟,孑影孤形。又回头看那日光,已是将落的时候,一片红霞,掩映在山头左近。那些寒鸦野鸟,或零乱沙滩,或娇啼树杪,心上好生伤感。于是复回旧路,走一步,懒于一步。瞧见那蒙葺细草,都变成满目凄迷,听见那碧水潺湲,竟仿佛人声哽咽。再看那些红桃绿柳,宝马香车,无一不是助他的咨嗟,伤他的怀抱。及至入了城,到人烟众多之地,又想起他的八抬大轿,后拥前呼,那一个敢不潜身回避?此刻和这些南来北往之人,挨肩擦臂,尊卑不分,成个甚么体统?心上越发不堪。一边行走,一边思想,已到了朱文炜门前。
张华正在那里眺望,看见如玉走来,连忙迎着问道:“大爷往那里去了一天?”
如玉听得,越发心上明白是做梦了。也不回答他,走入文炜大门内。因是初交,不好直入,只得和管门人说声。管门人一边让如玉进去,一边先去通报。
此时于冰众人,正在那里说笑如玉梦中的事业,大家都意料他是该回来的时候。听得管门人说:“温公子来了!”
于冰同文炜等接将出来。刚下了厅阶,如玉早到。金不换举手道:“驸马好快活!将我们一干穷朋友丢的冷冷落落,到此刻才肯回来,未免太寡情些了!”
如玉听罢,就和人劈心上打了一拳的一般,大为惊异。走到庭中,各揖让就坐。朱文炜道:“弟做着个京官,我这几间房子,真是蜗居斗室,甚亵驸马的尊驾。”
如玉道:“生员一入门来,众位俱以驸马长短相呼,这是何说?”
于冰道:“那华胥国也是一国之主,他女儿与公侯将相的女儿又自不同。你既与他做了女婿,非驸马而何?”
如玉听罢,呆了一会,又问道:“众位如何知道?”
于冰笑道:“你这三十余年的起结,我天天和看着一般。你若不信,我与你详细说说。”
便将如何见华胥国王,如何公主出题考试,如何配姻缘,做了大官,生了二子,结了亲家某某等,如何用火攻破了马如龙,如何封侯拜相,在甘棠镇享荣华数十年,如何新主疑忌,夺了兵权地土,如何步登高背叛,如何被铁里模糊拿住,斩首在金钱镇城头……你才醒过来,复回此处,可是不是?如玉听了,惊的瞠目咋舌,被众人大笑了几面,不由的又羞又气,变了面色,说道:“先生今日也以富贵许我,明日也以富贵许我,我温如玉命中若有富贵既是知己,便当玉成;若是我命中没有,何妨直说!为什么纯用邪术耍我?你既然耍了我,我到要和你要个真富贵哩!”
于冰鼓掌大笑道:“普天下痴想富贵的人,到你也可谓再无以复加!你听我明白告诉于你:你以督抚门第,巨万家私,被你一场叛案官司弄去了大半,你一该回头;你与尤魁贩货江南,弄得人离财散,着令堂含怨抱恨而死,你二该回头;你既卖祖房,又入嫖局,弄的盆干瓮涸,孤身无倚,一个金钟儿也为你横死惨亡,你三该回头。你原是落花流水,不堪的穷命,你却想的是出将入相,无比的荣华。我前已苦劝你两次,不意你痴迷不悟,今又入都中寻我。因此我略施小术,着你身为驸马,位至公卿,子孙荣贵,富可敌国,享极乐境遇三十余年,才坏于铁里模糊之手。你再想想:人生世上,那有个不散的筵席?富贵者如此,贫贱者亦如此。一日如此,虽百年也不过如此。好结局老死床被,坏结局身丧沟渠。铁里模糊刀头一落,正是与你做棒头大喝耳!你还算好机缘,遇着我,送你一场好梦儿做做。若是第二个人落魄到这步田地,求做这样一个好梦儿,亦不可得。你如今毫无猛省,还要向我要真实富贵。你从头至尾再加细想,还有像你梦中的富贵么?”
如玉听了这一篇言语,不由的惊心动魄,夹背汗流,扒倒在地连连顿首道:“我温如玉今日回头了!人生在世,无非一梦;寿长者为长梦,寿短者为短梦。可知穷通寿夭,妻子儿孙,以及贪痴恶欲,名利奔波,无非一梦也。此后虽真有极富极贵吾不愿得之矣!”
连城璧掀着胡子大笑道:“这个朋友,此刻才吃了橄榄了。”
冷于冰用手扶起,笑问道:“你可是真回头,还是假回头?”
如玉道:“既知回头,何论真假?”
于冰道:“你回头要怎么?”
如玉道:“愿随老师修行,虽海枯石烂,此志亦不改移。成败死生,任凭天命。”
于冰道:“你既愿修行,且让你再静养一夜,明早再做定归。只是你将我的符并二帖扯碎,叫着我的名字大动怒,未免处置我太过些。”
如玉也不敢回答。
家人们拿入酒来,如玉定要与于冰等同坐,朱文炜又不肯依。如玉道:“我如今是修行的人,岂有还同朱老爷吃荤菜之理?”
于冰笑道:“就是要修行,也不在这一顿饭上。今日朱先生与你收拾酒席接风,你须领他的厚意。”
如玉方与朱文炜坐了一桌,城璧、不换与于冰是一桌。吃酒中间,文炜又问起如玉梦中话来,如玉此时也不回避了,遂从头至尾细细的陈说,比于冰说的更周全数倍。城璧等俱各说奇道异,称妙不已。把一个朱文炜欣羡的了不得,若不是有家室牵连,也就跟于冰出家了。
到了定更后,仍是照常安歇。夜至二更,于冰等正在东房里打坐,听得西房里有人哭泣起来。城璧道:“这必是温如玉后悔出家了,再不就是他想起梦中荣华,在那里哭啼。”
不换道:“我去听他一听。”
待了好一会,不换入来,城璧道:“可是我说的那话么?”
不换道:“你一句也没说着。他如今是绝意出家,身边还带着三四百银子,都赏了张华,着他逢时节,与他祖、父坟前上个祭。那张华跪在地下,哭着劝他还家,说了许多哀苦话。我听了,到有些替他感伤。”
城璧道:“到明日看他何如?”
次日天一明,如玉便过东房来坐下。于冰道:“我们此刻就要别了东家起身,你还是回家,或是在都中另寻事业,还是和我们同走?”
如玉道:“昨日于老师前已禀明下悃,定随老师出家。都中还有何事业可寻?”
于冰道:“张华可舍你去么?”
如玉道:“我昨晚与他说的斩钢截铁,他焉能留我?”
于冰道:“我们出家人,都过的是人不能堪的日月,你随我们一年半载,反悔起来,岂不两误?”
如玉听了,又跪下道:“弟子之心,可贯金石。今后虽赴汤蹈火,亦无所怨!”
说罢,又连连顿首。于冰扶起道:“老弟不必如此称呼,通以弟兄呼唤可也。”
少刻,文炜出来,于冰等告别,并嘱林公子出场后,烦为道及。文炜道:“小侄亦深知老伯不能久留,况此别又不知何日得见,再请住一月,以慰小侄敬仰之心。”
于冰笑道:“不但一月,即一日亦不能如命。”
正说着,张华走来,跪在文炜面前,将晚间如玉话,并自己劝的话,哭诉又一遍,求文炜替他阻留。文炜问如玉道:“老世台主意若何?”
如玉道:“生员心如死灰,无复人世之想。虽斩头断臂,亦不可改移我出家之志。”
又向张华道:“你此刻可将银子拿去起身。我昨晚亦曾说过,你只与我先人年年多拜扫几次,就是报答我了。”
张华还跪着苦求,文炜道:“你主人志愿已决,岂我一言半语所能挽回?”
张华无奈,只得含泪退去。
于冰道:“我们就此告别罢。连日搅扰之至!”
朱文炜又苦留再住十日,于冰也不回答,笑着往外就走。朱文炜连忙拉住衣袖道:“请老伯暂留一天,房下还有话禀,就是小侄,也还问终身的归结,并生子的年头。”
于冰道:“你今年秋天,恐有美中不足,然亦不过一二年,便都是顺境了。生子的话,就在下月,定产麟儿。”
原来姜氏已早有身孕,四月内就该是产期。文炜听了,钦服之至,拉住于冰,总是不肯放去。于冰无奈,只得坐下。文炜又问终身事,于冰笑而不答。少刻,姜氏要见于冰,请朱文炜说话。文炜出了厅屋,向家人们道:“你们可轮班在大门内守候,若放冷太爷走了,定必处死。我到里边去去就来。”
家人们守候去了。
于冰见庭内无人,向城璧等道:“我们此刻可以去矣。”
城璧道:“只恐他家人们不肯放行。”
于冰用手向厅屋内西墙一指,道:“我们从此处走。”
城璧等三人齐看,见那西墙已变为一座极大的城门。于冰领三人出了城门,一看已在南西门外。往来行人,出入不绝。朱文炜家已无踪影矣。金不换乐的满地乱跳,温如玉目瞪神痴,连城璧掀髯大笑道:“这一走,走的神妙不测,且省了无数的脚步。”
又笑问于冰道:“此可与我们在温贤弟家从大磁罐内走,是一样法术么?”
于冰道:“那是遮掩小术,算得甚么?此系金光那移大转运,又兼缩地法,岂遮掩儿戏事也?”
四人向西同走,约有六七里,于冰远远的用手指向温如玉道:“那座花园,可是你做梦的地方么?”
如玉道:“正是此地。”
于冰道:“你日前是做梦,我今领你去寻梦,还你个清清楚楚,你可一心学道,永解狐疑。”
如玉大喜道:“怎么,这梦还可以寻得么?我到要明白明白。”
四人说着,入了那座园门。那种菜的人,见三四人同一道士入来,忙问道:“做什么?”
于冰道:“我们闲看看就去。”
于冰指着那木牌坊,问如玉道:“你昨日做梦时,可见一座牌坊么?”
如玉道:“我梦中果见有一座牌坊,却比这牌坊高大华美数百倍,并不是这样不堪的形象。”
于冰笑道:“不独这牌坊,率皆如此。此即华胥国界,即是你睡觉入梦之地也。你看,上面还有‘大觉园’三字。大觉,乃知觉之谓,莫认作睡觉之觉也。不但你在梦中,即今日你亦未识‘大觉’二字耳。”
又走了几步,见东南一带土冈,有一丈四五尺长,二尺半高下,斜横在西北。于冰道:“此土冈,即你用火攻计烧马如龙军兵地也。”
如玉道:“我梦中在此岭扎营,曾问众将,伊等言此岭长二十五里,宽二三里四五里不等。今止数尺,何大相悬绝如此?”
于冰笑道:“此即梦中所见牌坊之类,不过藉名色形像点缀而已。你若必如梦中长大宽阔,你看这园子能有几亩?”
过了土冈,见前面有几株甘棠树,于冰道:“此即你荣封甘棠侯、大丞相、享荣华之地也。”
金不换道:“温贤弟,你何不高叫几声,看你所配的兰牙公主,并你两个儿子延誉、延寿,他们有点响应没有?”
如玉面红耳赤的道:“岂有此理!此皆莫须有的鬼话!”
于冰道:“你梦中的华胥国王,以及海中鲸、黄河清、步登高、铁里模糊,并你妻子、家奴,这皆是你梦中所遇之人,原无指证,谓之鬼话,未为不可。难道你梦中所到的地方,并此刻我指与你的地方,都与你梦所经历者相合,也还算做鬼话不成么?”
如玉道:“梦中境像,皆真山真水;城池树木,宫殿楼台,是何等阔大,何等规模,那里是这样弹丸之地,便将几千百里包括?”
于冰道:“我适才言,不过藉此地所有名色形像,点缀梦景而已,怎么你还拘执如此?我再说与你魂之所游,即你心之所欲,所欲焉能如意?因此与你符箓一道,始能成就你心之所欲也。因此把眼前所到之极小境界,皆比为无极之大境界。假如你无我的符,焉能做的了此梦也?”
说罢,又指着那几十堆大小石头道:“你看这些石头,高高下下,堆成假山,此即你梦中之太湖山,遣白、赤二将埋伏之地也。”
又指着浇畦水渠道:“此渠系灌菜之水道,春夏用他时多,至科则无用矣。此即你梦中之神水沟也。”
往东南走了几步,见一无水池子,于冰道:“此即你梦中之所争之荷花池界,公主之汤沐邑也。”
从东南回来四五步内,有一小土坡,细草蒙茸,于冰道:“此即你梦中之倩女坡,即老弟被擒之地也。”
相隔一两步远,有几株金钱花,于冰道:“此即你梦中之金钱镇,铁里模糊斩你于此,醒梦之地也。”
如玉长叹了一声。
于冰说罢,笑着回来。如玉道:“今所指诸地,皆与我所梦相符,可见我之魂魄总不出这园外。只是华胥、槐阴、邯郸等国,在此园中何处?”
于冰道:“你既是秀才,难道连四大梦的书,并本人自立的传文,还有后人做的传文,而邯郸、槐阴二梦,且有戏文,历来扮演,怎么你就都没见过么?华胥国系黄帝梦游之所,醒后至数年,果游此国,其山川、宫室、花卉、草木,无一不与前梦相合。邯郸系直隶地界,吕纯阳授枕于卢生,梦享富贵五十余年,醒后黄粱尚未做熟,故又谓之黄粱梦。槐阴梦,是淳于棼梦入大槐安国,其大概与卢生相同,由大丞相降职知府,治理南柯郡,醒后在一大槐树下,旁有蚁穴,南柯即槐树南一小枝也,又名之为南柯梦。二子皆因仙人点化入梦,后来俱成仙道。我今着你做甘棠梦,醒后归吾教下,或者将来得如卢生等有成,亦未敢定。以上华胥、槐阴、邯郸三国,不过于你梦中,借其名一用耳。就如你梦中之游魂关,是言你魂魄游行了。佳梦关,是言你做好梦也。驻玉关,你名如玉,言玉驻于此关,不得再入槐阴国征讨也。倩女坡,借倩女离魂之名,言你之魂离也。这些名色,你梦中也该一想。今你着我指与你各国各关下落,要和园中所有之甘棠岭、太湖山、荷花池等处一般,都要看在眼内,我该从何处着你看起?”
连城璧道:“今日大哥领你来寻梦,是怕你思念梦中荣华富贵,妻子情牵,弄的修道心志不坚,所以才件件桩桩,或实或虚,都说明白,教你今后再不可胡思乱想,你当和你闲散心来么?”
如玉道:“二哥指教的甚是。”
四人走了园子来。又来了二三里,到一无人之地。于冰道:“温贤弟,你听我说。我们的洞有两处,一处在湖广衡山,名玉屋洞,这是紫阳真人炼丹之所,我们不过借住几年;一处就是你山东泰山,名琼岩洞,现有超尘、逐电两个在那里修炼。我们如今要回玉屋洞去,若将你也带在那里,朝夕与我们相伴,未免分你的志。亦且修行的人,必须先受些苦难,扩充起胆量来,方能入道;若留你在人世庵观寺院居住几年,先淡薄你的脾胃,又恐你为外物摇动,坏了身心。我们这三个人,谁肯在烟火场中伴你?我思算至再,意欲送你到泰安琼岩洞,同超尘、逐电等修炼数年后,再做商酌。你意如何?”
如玉道:“任凭吩咐,不但琼岩洞还有人在那边,即无一人,即已出家,也就拣择不得了。我就到琼岩洞中去。只求三位六驾,时常看看我,我就感戴不尽。但不知超尘、逐电是些什么人?”
于冰笑道:“你到那里便知。”
随向城璧道:“你可送他到琼岩洞,传与他凝神御气之法。待他呼吸顺妥,你再回玉屋洞中。”
城璧道:“温贤弟人必聪明,凝神御气,看来不用费力。只是他一身血肉未去一分,云断驾不起;若步行同去,琼岩洞道路有许多危险地方,和他走两个月,还定不住怎么。”
于冰大笑道:“他若驾不起云,仙骨也不值钱了,我还渡他怎么,你刻下试试瞧!”
城璧将如玉左臂扶住,着他闭住眼,口中念念有词,顷刻云雾缭绕,喝声:“起!”
同如玉俱入太虚。
金不换连声喝彩道:“亏他!亏他!一日未曾修炼,起去时毫不费力,竟与我们一般,果然这仙骨不可不长几段在身上。将来到怕他要走到我们头前。”
于冰道:“他若心上将世情永绝,必先你二人成就几十年。你此刻可仍回京中,弄几两银子,与温贤弟买些皮夹棉衣、暖鞋、暖帽,为御寒之具,皮衣分外多些才好。他纯是血肉之躯,非你二人可比。再买办几十石米,吩咐超尘等,着他两个轮流砍柴做饭,早晚要殷勤扶侍他。他是豪奢子弟出身,焉能受得艰苦?过三五年后,再着他自己食用。若他两个少有怠忽,我定行逐出洞去,说与他们知道。我今去骊珠洞,教化修文院雪山二女,以报他指引《天罡总枢》之情。”
说罢,驾云赴虎牙山去了。
不换在地下,挝了一把土,向坎位上一洒,口中秘诵法语,喝道:“那物不至,更待何时?”
须臾,袍袖内丁当有声,倒出五六十两银子来。将头上毡帽取下,把银子装在里面,揣在怀中。又从怀中将道冠取出,戴在头上,口中鬼念道:“万一朱御史差人向南西门寻找,遇着时,我只将脸儿用袍袖一遮,他们见是道士,便不理论了。”
于是复回旧路。
再说朱文炜从内院走出,请于冰与姜氏说话,不意遍寻无踪,心知去了。张华着急之至,哭请文炜示下,文炜劝他回山东,还赏了二两盘费,又留他住了一天,方才回去。
正是:
斩断情缘无挂碍,分开欲海免疑猜。
他年再世成仙道,皆是甘棠梦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