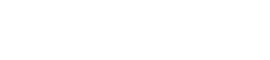第四十八回
听喧淫气杀温如玉 恨讥笑怒打金钟儿
词曰:
且去听他,白昼闹风华。淫声艳语嗳呀呀,气杀冤家。
一曲琵琶干戈起,打骂相加。郎今去也各天涯,心上结深疤。
——右《珠沉渊》。
话说金钟儿去后,温如玉随即穿衣服。苗秃道:“我与你要洗脸水去。”
少刻,如玉到前边,张华收拾行李。郑三家两口子,说好说歹的才将如玉留下;又暗中嘱咐金钟儿,在两处儿都打照着,休要冷淡了旧嫖客。如玉同众人吃了早饭,因昨夜短了睡,到后边困觉。
睡到午间,扒起到前院一看,白不见一个人,止有郑三在南房檐下,坐着打呼。原来苗秃子等同何公子家丁们,郊外游走去了。如玉走到庭房,正欲趁空儿与金钟诉诉离情。刚走到门前,将帘儿掀起,见门子紧闭。仔细一听,里面柔声嫩语,气喘吁吁,是个云雨的光景。又听得抽送之声,与狗舐粥汤相似。少刻声音更迫,只听得金钟儿百般乱叫,口中说死说活。
如玉听到此际,比晚前那一番更是难受,心上和刀剜剑刺的一般,长出了一口气。
走到后边,把桌子拍了两下道:“气杀!气杀!”
将身子靠在被褥上,发起痴呆来。好半晌,方说道:“总是我来的不是了。与这老忘八肏的做的是什么寿!”
猛见玉磬儿笑嘻嘻的入来道:“大爷和谁说话哩?”
如玉道:“我没说什么。请坐。”
玉磬儿道:“东庭房着人占了,大爷独自在此,不寂寞么?”
如玉道:“也罢了。”
玉磬儿道:“他们都游走去了,止有何公子在金妹子房中睡觉。我头前来看大爷,见大爷睡着了,不敢惊动。”
如玉道:“这何公子到你家,前后共几天了?”
玉磬儿道:“连今日十八天。”
如玉道:“不知他几时起身?”
玉磬儿微笑道:“这到不晓的。”又道:“他两个正是郎才女貌,水乳相投。这离别的话,也还说不起哩。”
如玉道:“苗三爷与你最久,他待你的情分何如?”
玉磬儿道:“我一生为人,大爷也看得出,谁疼怜我些,谁就是我的恩人,只是自己生的丑陋,不能中高贵人的眼,这也是命薄使然。”
如玉道:“你若算丑陋人,天下也没俊俏的了。”
玉磬儿笑道:“大爷何苦玩弄我?只是大爷到这里来,金妹子又无暇陪伴。到教大爷心上受了说不出的委曲。”
如玉道:“此番你妹子,不是先日的妹子了,把个人大变了。我明日绝早走;将来他不见我,我不见他,他还有什么法儿委曲我?”
玉磬儿道:“嗳哟!好大爷,怎么把斩头滴血的话都说出来?我妹子今年才十九岁,到底有点孩子性。将来何公子走了,他急切里也没个如意的人,除了大爷,再寻那个?”
如玉冷笑道:“我还不是就近的毛房,任人家屎尿哩!不是你三叔和你三婶儿,再三苦留,我此刻也走出六十里去了。”
两人正叙谈着,忽听得外面有人说笑。玉磬儿道:“我且失陪大爷。”一直前边去了。
少刻,前边请吃饭,大家齐到庭上。只见郑三家老婆入来,看着温如玉,向何公子道:“承这位温大爷的盛情抬举我,因为我的贱辰,补送礼物,已经过分了;又拿来许多的缎子衣服,我昨日细看,到值六七十两。只是小地方儿没有什么堪用的东西,今日不过一杯水酒,少伸谢意。”又嘱咐金钟、玉磬儿道:“你两个用心陪着,多吃几杯儿。”说罢出去了。
何公子道:“昨日小弟胡乱僭坐,今日是东家专敬,温兄又有何说?”
萧麻子道:“今日是不用逊让的,自然该温大爷坐,完他东家敬意。何大爷对坐,我与老苗在上面横头,他姊妹两个在下面并坐就是了。”
说罢,各一一入坐。不多时,杯泛琼苏,盘堆珍品;兰肴绮馔,摆满春台。如玉存心看金钟儿举动,见他磕了许多瓜子仁儿,藏在手内;又剥了个元肉丸儿,将瓜子仁都插在上面;不知什么时候,已暗送与何公子。又见何公子将元肉同瓜子仁儿浸在酒杯内,慢慢的咀嚼。如玉甚是不平,踌躇了一会。苗秃子见如玉出神,用手在肩上拍了一下,说道:“你不吃酒,想甚么?”
如玉道:“我想这乐户家的妇女,因是朝秦暮楚,以卖俏迎奸为能。然里头也有个贵贱高低。高贵的,止知昏夜做事;下贱的,还要白日里和人打枪,与没廉耻的猪狗一般。你看那猪狗,不是青天白日里闹么?”
金钟儿听了,知道午间的事必被如玉听见,此刻拿话讽刺,便回答道:“猪狗白日里胡闹,虽是没廉耻,他到的还得些实在。有那种得不上的猪狗,在傍边狂叫乱咬,那样没廉耻,更是难看。”
萧麻子急急瞅了一眼,如玉登时耳面通红,正要发作,苗秃子大笑道:“若说起打枪来,我与玉姐没一天白日里没有。”
玉磬儿道:“你到少拿这臭屁葬送人。我几时和你打枪来?”
苗秃子道:“今日就有。我若胡葬送你,我就是郑三的叔叔。”
何公子大笑道:“这话没什么讨便宜处。”
苗秃道:“我原知道不便宜,且乐得与他姐妹两个做亲爷。”
玉磬儿道:“我只叫你三哥哥。”
萧麻子道:“你们莫乱谈,听我说。今日东家一片至诚心,酬谢温大爷,我们极该体贴这番敬客的意思。或歌或饮,或说笑话儿,共效嵩呼。”
何公子道:“萧兄说得甚是!快拿笛笙、鼓板、琵琶、弦子来,大家唱唱。”
众人你说我笑,将如玉的火压下去了。
须臾,俱各取来,放在一张桌子上。萧麻子道:“我先道过罪,我要做个令官,都要听我的调遣。我们四人普行吃大杯;金姐、玉姐每遍斟三分;我们都是十分杯子。要转着吃,次第轮流。每吃一杯,唱一曲。上首坐的催下首坐的。干迟者罚一大杯。你们以为何如?”
苗秃道:“这个令到也老实公道。只是不会唱的该怎么?”
萧麻子道:“不会唱的,吃两杯免唱。爱唱的,十个八个只管唱。若唱的不好,听不敢过劳。”
说罢,都斟起大杯来。如玉道:“我的量小,吃不动这大杯。每次斟五分罢。”
萧麻子道:“这话不行。就如我也不是怎么大量,既讲到吃酒,便醉死也说不得。”
于是大家都吃起来。
萧麻子道:“令是我起的,我就先唱罢。”
金钟儿道:“我与你弹上琵琶。”
萧麻子道:“你弹上,我到一句也弄不来了。到是这样素唱为妥。”
说着,顿开喉咙,眼看着苗秃子唱道:
《寄生草》:我爱你头皮儿亮,我爱你一抹儿光,我爱你葫芦插在脖子上,我爱你东瓜又像西瓜样,我爱你绣球灯儿少提梁,我爱你安眉戴眼的听弹唱,我爱你一毛儿不拔在嫖场上浪。
众人听了,俱各鼓掌大笑。
苗秃子着急道:“住了,住了,你们且止住笑,我也有个《寄生草》,唱唱你们听。”
唱道:
你好似莲蓬座,你好似马蜂窝,你好似穿坏的鞋底绳头儿落,你好似一个核桃被虫钻破,你好似石榴皮子坑坎儿多,你好似臭羊肚儿翻舔过,你好似擦脚的浮石着人嫌唾。
众人也都大笑。何公子道:“二位的曲子,可谓工力悉敌,都形容的有点趣味。”
萧麻子道:“快与苗三爷斟起一大杯来。”
苗秃子道:“为什么?”
萧麻子道:“罚你。”
苗秃子道:“为什么罚我?”
萧麻子道:“罚你个越次先唱。我在你下首,我是令官,我唱了,就该何大爷;何大爷唱后,是金姐、玉姐、温大爷,才轮着你。你怎么就先唱起来?到该你唱的时候,那怕你唱十个二十个也不妨,只要你肚里多。若嫌你唱的多罚你,就是我的不是了。”
何公子道:“令不可乱,苗兄该吃这一杯。”
萧麻子立逼着苗秃吃了。萧麻子又道:“再与苗三爷斟起一大杯来。”
苗秃子着忙道:“罚两杯么?”
萧麻子道:“头一杯,是罚你越次先唱;这第二杯,罚你胡乱骂人。”
苗秃子大嚷道:“这都是奇话。难道说,只许你唱着骂我么?”
萧麻子道:“我不是为你骂我。你就骂我一千个,也使得;只要你有的骂。只是这金姐脸上,也有几个麻子。你就骂,也该平和些儿,怎么必定是石榴皮、马蜂窝、羊肚子、擦脚石,骂的伤情利害,到这步田地?若是玉姐有几个麻子,你断断不肯骂出来。”
金钟儿粉面通红道:“这叫个穷遮不得,富瞒不得。我这脸上,原也不光亮,无怪乎苗三爷取笑我。”
苗秃子听了,恨不得长出一百个嘴来分辨,忙说道:“金姐,你休听萧麻子那疤肏的话,他是信口胡拉扯。”
萧麻子大笑道:“金姐你听听,越发放开口的骂起咱两个是疤肏的来了。”
苗秃子打了萧麻子两拳,说道:“金姐,你的麻子,就和月有清阴,玉有血斑的一样,真是天地间秀气钟就的灵窟,多几个儿不可,少几个儿也不可,没一个儿更不可。就是用凤衔珠、蛇吐珠、僻尘珠、玄鹤珠、骊龙珠、象网珠、如意珠、滚盘珠、夜明珠、照乘珠,一个个添补起来,也不如这样有碎窟小窝儿的好看,那里像萧麻子的面孔,与缺断的藕根头相似,七大八小,深深浅浅,活怕死人!”
萧麻子道:“任凭你怎么遮饰,这杯酒总是要罚的。”
苗秃被逼不过,只得将酒一气饮干,说道:“罢!罢!我从今后,连萧麻子也不敢叫你了,我只叫你的旧绰号罢。”
何公子道:“萧兄还有旧绰号么?”
苗秃子道:“怎么没有?他的旧绰号叫象皮龟。”
众人听了,俱备大笑。
以下该何公子唱了。何公子将酒饮干,自己拿起鼓板来,着他跟随的家人们吹上笙笛,唱了《阳告》里一支《叨叨令》。
如玉道:“何兄唱的,抑扬顿挫,真堪裂石停云,佩服,佩服。”
何公子道:“小弟的昆腔,不过有腔有板而已,究竟于归拿字眼、收放吞吐之妙,无一点传授,与不会唱的门外汉无异。承兄过誉,益增甲颜。”
次后该金钟儿唱了。金钟儿拿起琵琶,玉磬儿弹了弦子,唱道:
《林梢月(丝弦调)》:初相会,可意郎,也是奴三生幸大。你本是折桂客,误入章台,喜的奴竟夜无眠,真心儿敬爱。你须要体恤奴怀。若看做残花败柳,岂不辜负了奴也。天呀,你教奴一片血诚,又将谁人堪待?
萧、苗二人,一齐叫好,也不怕把喉咙喊破。温如玉听了,心中恨骂道:“这淫妇奴才,唱这种曲儿,他竟不管我脸上下得来下不来。”
金钟儿唱罢,玉磬儿接过琵琶来,将弦子递与金钟儿,改了弦唱道:
《桂枝香(丝弦调)》:如意郎,情性豪,俊俏风流。尘寰中最少。论第督抚根苗。论才学李杜清高。恨只恨和你无缘叙好。常则愿席上樽前,浅斟低唱相调谑。一觑一个真,一看一个饱。虽然是镜花水月,权且将门解愁消。
众人也赞了一声好。
底下该温如玉唱了。如玉道:“我不唱罢。”
众人道:“却是为何?”
如玉道:“我也欲唱几句昆腔。一则有何兄的珠玉在前,二则小弟的曲子非一支半文所能完结,诚恐咶唣众位。”
众人道:“多多益善,我们大家洗耳静听佳音。”
如玉自己打起鼓板,放开喉咙唱道:
《点绛唇》:海内名家,武陵流亚。萧条罢,整日嗟呀,困守在青毡下。
《混江龙》:俺言非夸大,却九流三教尽通达。论韬略孙吴无分,说风骚屈宋有华。人笑俺挥金掷玉贫堪骂,谁怜我被骗逢劫命不佳。俺也曾赴棘闱,含英咀华;俺也曾入赌局,牌斗骰挝;俺也曾学赵胜,门迎多士;俺也曾仿范公,麦赠贫家;俺也曾伴酸丁,笔挥诗赋;俺也曾携少妓,指拨筝琶;俺也曾骑番马,飞鹰走狗;俺也曾醉燕氏,击筑弹挟;俺也曾效梨园,涂朱傅粉;俺也曾包娼妇,赠锦投纱;俺也曾搂处子,穴间窃玉;俺也曾戏歌童,庭后摘花;俺也曾弃金帛,交欢仕宦;俺也曾陈水陆,味尽精华。为什么牡丹花,卖不上山桃价?龟窝里遭逢淫妇,酒席上欺负穷爷。
众人俱各鼓掌道好。金钟儿笑道:“你既到这龟窝里,也就说不得什么穷爷、富爷了。请吃酒罢,曲子也不敢劳唱了。”
如玉道:“酒到可以不吃,曲子到要唱哩。”
又打起鼓板来,唱道:
《油葫芦》:俺本是风月行一朵花,又不秃,又不麻。
(苗秃子笑向萧麻道:“听么,只用一句,把我和你都填了词了。”)
锦被里温存颇到家,你纤手儿搦过俺弓刀把,柳腰儿做过俺旗枪架。枕头花两处翻,绣鞋尖几度拿。快活时说多少知心话,恁如今片语亦无暇。
萧麻子道:“前几句叙的,甚是热闹;后几句叙的可怜。看来必定这金姐有不是处。”
金钟儿笑了一笑。如玉又唱道:
《天下乐》:你把全副精神伴着他。学生待怎么,他是跌破的葫芦嚼碎的瓜。谎的你到口苏,引的你过眼花。须堤防早晚别你,把征鞍跨。
何公子大笑道:“温兄倚马诗成,真是盛世奇才,调笑的有趣之至。就是将小弟比做破葫芦、碎西瓜,小弟心上也快活不过。”
如玉又唱道:
《那吒令》:你见服饰盛些,乱纷纷眼花。遇郎君俏些,艳津津口夺。对寒儒那些,闷厌厌懒答。论银钱让他多,较本事谁行大,我甘心做破釜残车。
何公子毫不介意,只是哈哈大笑,拍手称妙不绝。如玉又唱道:
《鹊踏枝》:你则会鬓堆鸦,脸妆霞。止知道迎新弃旧,眉眼风华。他个醉元规,倾翻玉斝,则俺这渴相如,不赐杯茶。
何公子道:“相如之渴,非文君不能解。小弟今晚,定须回避;不然,亦不成一元规矣。”
说罢大笑。如玉唱道:
《寄生草》:对着俺誓真心,背地里偷人嫁。日中天犹把门帘挂,炕沿边巧当鸳鸯架。帐金钩摇响千千下,闹淫声吁喘呼亲达。怎无良连俺咳嗽都不怕。
何公子听了,笑的前仰后合,不住口的称道奇文妙文,赞扬不已。苗秃子道:“怪道他今日鬼念打枪的话说,不想他是有凭据的。”
金钟儿笑道:“你莫听他胡说,他什么话儿编造不出来?”
苗秃子道:“你喘吁着叫亲达,也是他编造的?连人家咳嗽都顾不得回避了。”
众人都笑起来。萧麻子道:“你们悄声些儿,他这曲儿,做的甚有意思、有趣味。我们要禁止喧哗。”
如玉又唱道:
《尾声》:心痒痛难拿,唱几句拈酸话。恁安可任性儿,沉李浮瓜。到而今把俺做眼内疔痂。是这般富炎穷凉,新真旧假。拭目恁那蛛丝情尽,又网罗谁家?
如玉唱完,众人俱各称羡不已,道:“这一篇醋曲撒在嫖场内,真妙不可言!”
何公子道:“细听数支曲子,宫商合拍,即谱之梨园,扮演成戏,亦未为不可。又难得有这般敏才,随口成文,安得不着人服杀!”
苗秃子道:“扮金姐的人,到得一个好小旦;不然,也描写不出他这迎新弃旧的样儿来。”
金钟儿道:“苗三爷也是一这样说,我竟是个相与不得的人了。我也有一支曲儿,请众位听听。”
萧麻子道:“请吐妙音。”
金钟儿把琵琶上的弦,都往高里一起,用越调高唱道:
《三煞双调琥珀猫儿坠加字啰啰腔》:你唱的是葫芦咤,我听了肉也麻。年纪又非十七八,醋坛子久该倒在东厕下。说什么先有你来后有他,将督院公子抬声价。你可知花柳行爱的是温存 、重的是风华。谁管你祖上的官儿大。 (一煞。)
何公子等听了,俱不好意思笑。萧麻子摇着头儿道:“这位金姐,也是个属鹌鹑的,有几嘴儿斗打哩!”
金钟儿唱道:
自从他那晚住奴家,你朝朝暮暮无休暇。存的是醋溜心,卜的是麻辣卦。筷头儿盘碗上打,指甲儿被褥上挝,耳朵儿窃听人说话。对着奴冷笑热夸,背着奴鬼嚼神查。半夜里喊天振地叫张华,梦魂中惊醒教人心怕。(二煞)
奴本是桃李春风墙外花,百家姓上任意儿钩搭。你若教我一心一信守一人,则除非将奴那话儿缝杀。(三煞)
金钟儿却要唱下句,当不得众人大笑起来。苗秃子道:“若将金姐那话缝杀,只怕两位公子要哭死哭活哩!”
萧麻子笑说道:“不妨,不妨,只用你将帽儿脱去,把脑袋轻轻的一触,管保红门再破,莲户重开。”
苗秃子恰要骂,金钟儿又唱道:
《尾声》:从来说旧家子弟多文雅,谁想有参差。上品的凝神静气,下流的磨嘴粘牙。
如玉因头前有猪狗长短话,已恨怒在心;又听了那两段,早已十分不快;今听了上品下流的话,不由的心头火起,问金钟儿道:“你把这上品、下流的话,与我讲一讲。”
金钟儿道:“我一个唱曲儿,有什么讲论?”
苗秃子笑道:“你们个相与家,甚么话儿不说,才讲论起字眼来了。”
如玉冷笑道:“你这奴才着实放肆,着实不识好歹!”
金钟儿道:“你到少要奴才长短的骂人。”
如玉道:“你原是娼妇家,不识轻重的奴才。我骂你奴才,还是抬举你哩。”
金钟儿向众人道:“人家吃醋,都在心里。我没见他这吃醋,都吃在头脸上,连羞耻都不回避。”
萧麻子道:“禁声些儿,你两个虽然是取笑,休教何大爷的尊纪笑话。”
金钟儿又欲说,不防如玉隔着桌子,就是一个嘴巴,打的金钟儿星眸出火,玉面生烟;大叫了一声,说道:“你为什么打我?我还要这命做什么?”
说着掀翻了椅子,向如玉一头撞来。萧麻子从后抱住。如玉赶上来,又是一个嘴巴,打的金钟儿大喊大叫。如玉又扬拳打下。苗秃子急向金钟儿面前一遮,拳落在苗秃头上,帽儿坠地。萧麻子将金钟儿抱入房里去了。苗秃子两手揉着秃头,说道:“好打!”
郑三家两口子从后面两步做一步跑来。郑三家老婆问玉磬儿道:“你妹子和谁闹?”
玉磬儿不敢隐瞒,说道:“适才被温大爷打了一下,萧大爷抱入东房去了。”
郑婆子笑说道:“好温大爷,我家女厮年青,有不是处指驳他,防备人家动手脚,怎么你老人家才动起手脚来了?岂不失雅道?”
如玉气的也回答不出。只听得金钟儿在房内大哭,口里也有些不干不净的话。郑三听得,连忙拉了他老婆,到房内教训他闺女去了。温如玉走出街门,哈喝着张华,收拾行李。苗秃子随后跟来,如玉已急急的出堡门去了。
正是:
讴歌逆耳祸萧墙,义海情山一旦忘。
水溢蓝桥应有会,两人权且作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