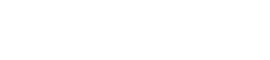第十九回
兄归乡胞弟成乞丐 婶守志亲嫂做媒人
词曰:
胸中千种愁,挂在斜阳树。绿叶阴阴自得春,恨满莺啼处。
不见同床婿,偏聆如簧语。门户重重叠叠云,山隔断西川路。
——右调《百尺楼》。
且说朱文炜别了林岱,出了新都县,路上问段诚道:“我这件事做的何如?”
段诚道:“真是成德之事。只怕大相公有些闲言语。”
文炜道:“事已做成,由他发作罢了。”
文炜入了金堂县,到慈源寺内。文魁道:“你两个要的账目何如?”
文炜道:“共要了三百二十七两。”
文魁听了大喜道:“我算的一点不差,怎便多要出十两?银子成色分两何如?”
文炜道:“且说不到成色分两上。有一件事要禀明哥哥。”
文魁着惊道:“有什么事?”
文炜就将遇林岱夫妻拆散,舍银帮助的话。文魁也等不得说完,忙问道:“只要捷近说,银子与了他没有?”
文炜道:“若不是与了他,他夫妻如何完聚?”
文魁道:“到底与了他多少?”
文炜道:“三百二十七两全与了他。”
文魁又忙问段诚道:“果然么?”
段诚道:“句句是实。”
文魁扑向前,把文炜脸上就是一掌。文炜却要哀恳,不防右脸上又中了一掌。老和尚师徒一同来劝解,文魁气的暴跳如雷,道:“我家门不幸,养出这样痴子孙来!”
复将文炜帮助林岱的话,与僧人说了一遍,又赶上去打。两僧人劝了一会,也就散了。文魁倒在床上,拍着肚子大叫道:“可怜往返八九千里,一场血汗勤劳,被你一日花尽。”
又看着段诚骂道:“你这该剐一万刀的奴才!他就做这样事体,要你何用?”
跑下来又将段诚打了一顿,从新倒在床上喘气。待了一会,又大嚷道:“你就将三钱二钱,甚至一两二两,你帮了人,我也还可恼,怎么将三百二十七两银子,一戥盘儿送了人家?我就教你……”
将文炜揪过来,又是几拳,倒在床上睡觉去了。文炜与段诚面面厮窥,也没个说的。
不多时,文魁又拍手打掌的大骂道:“你就是王百万家,也不敢如此豪奢。若讲到积阴德,满朝的王公大臣他还没有钱?只用着几个人,驮上元宝,遍天下散去罢了。”
又问道:“你的行李放在那里?”
文炜不敢言语。文魁再三又问,段诚道:“二相公说,多的已经费了,何况少的。为那姓林的没盘费去荆州,将行李当了十四两银子,也送与他了。”
文魁大笑道:“我原知道,不如此不足以成其憨。像你两个,一对材料,真是八两半斤。其实跟了那姓林的去,我到洒脱。这一共是三百二十七两银子,轻轻的葬于异姓之手。”
说罢,捶胸顿足,大哭起来。文炜道:“哥哥不必如此,银子已经与了人家,追悔莫及,总是兄弟该死。”
文魁道:“不是你该死,到是我该死么?罢了,我越想越气,我今日和你死在一处罢。”地下放着一条铁火棍,拿起来就打。
段诚急忙架住道:“大相公,这就不是了。当日老主人在日,二相公就有天大的不是,从未弹他一指,大相公也该仰体老主人之意。今日打了三四次,二相公直受不辞,做兄弟的道理,也就尽在十二分上。怎么才拿铁器东西打起了?大相公顽钱,曾输过好几个三百两,老主人可打过大相公多少次?”
文魁道:“你敢不教我打他么?你不教我打他,我就打你。”
段诚道:“打我到使得。”
文魁将段诚打了两火棍,又要去打文炜。段诚道:“大相公不必胡打,我有几句话要说。”
文魁道:“你说你说。”
段诚道:“二相公是老主人的儿子,大相公的胞弟,老主人若留下一万两银子,少不得大相公五千,二相公五千。就是今日这事,也费的是人情天理钱,权当像大相公赌钱输了。将来到分家的时候,二相公少分上三百二十七两就罢了。是这样打了又打,总不念手足情分,也该往祖父身上想想,难道这家私都是大相公一个的么?”
几句话,说的文魁睁着眼,呆了一会,将火棍往地下一丢,冷笑道:“原来你两个通同作弊,将三百多银子不知鬼弄到那里去,却安心回来要与我分家。既要分家,今日就分。”
文炜道:“段诚不会说话,哥哥不必听他胡说。”
文魁道:“他是极为顾我的话,我怎么不听他?我和你在一处过日子,将来连讨吃的地方也寻不下。”
文炜道:“就是分家,回家中再商量。”
文魁道:“有什么商量?你听我分派。我们的家业止有二千两,住房到算着七百。我将住房分与你,我另寻住处。你帮了人家三百多两,二宗共是一千。你一千,我一千,岂不是均分?此名为一刀两断,各干其事。”
文炜道:“任凭哥哥。不但还与我一处住房,就一分不与我,也没得说。”
段诚道:“大相公算是将家业分完了?也再没别的个分法?”
文魁道:“能有多大的家业,不过三言两语,就是个停当。”
段诚道:“老主人家中的私囊,并器物衣服,且不必算。此番刘贡生银子,共本利一千三百余两,大相公早要到手中,寄放在本城德同铺内,也不向我们说声。家中三顷地,也值千余两,付之不言。老主人当年用银买的住房,止三百三十两,人所共知。如今算了七百两,要分与二相公,何不将此房第七百两银子,大相公拿去?世上没有这样个分法。”
文魁大怒道:“你这奴才晓得甚么!家有长子,犹之国有储君,理应该长子拣选,其余次子季子将均分,此天下之达道也。二千两家私,我若与他分不够一千之数,就是我有私心了。”
段诚道:“不公,不服。”
文魁怒极道:“你不服便怎么?从此刻一言为断,你两个到别处去住。若在此处住,我即另寻地方搬去。来虽同来,走要另走。我若再与你们见面,我真正不是个人娘父母养的。”
文炜哭说道:“就是兄弟少年冒昧,乱用银两,然已成之过,悔亦无及。哥哥着我们另寻住处,身边一分盘费没有,行李又当在新都,这一出去,总不冻死,定必饿死。哥哥与兄弟同胞手足,何忍将兄弟撇在异乡,自己另行回去。”
文魁道:“你是帮助人的,不论到那里,都有人帮你。任你千言万语,我的志愿已决。”说罢,气忿忿的躲在外边去了。
文炜向段诚道:“似此奈何?”
段诚道:“当日老主人在日,屡屡说他夫妻二人不成心术。此番就是不帮林相公,这三百多银子,他又有别的机谋,作分离地步。可惜相公为人太软弱,依小人主见,先请阖县绅士公评,分现在银钱器物。若公评不下来,次到本县前具呈控诉。量他也没什么七手八脚的本领,于情理王法之外制人。”
文炜道:“我一个胞兄,便将我冻饿死在外边,我也做不出告他的事来。请人说合调停,到还是一着。”
随即着段诚请素日与他哥哥相好者四五人,说合了六七次,方许了十两银子。言明立刻另寻住处,方肯付与。文炜无可如何,在朱昱灵前大哭了一场,同段诚在慈源寺左近寻店住下。说合人拿过十两银子来,文炜又脆恳他们代为挽回。
隔了两日,去寻文魁,僧人道:“从昨日即出门去了。”
第五日,文炜又去,文魁总不交一言。文炜在他身傍站了好半晌,只得回来。
又隔了四五天,文炜又去,老僧在院中惊问道:“二公子没与令兄同回乡去么?”
文炜道:“同回那里去?”
老僧道:“令兄连日,将所有家器大小等物变卖一空。前日晚上装完行李,五鼓时即起身。我问了几次,他说你同段二爷先在船中等候。我说你们都去,这灵柩作何归着?他说道路远,盘费实是不足,定在明年亲来搬。我以为你也同去了,怎还在此,这是何说?”
文炜道:“此话果真么?”
老僧用手指着道:“你看他房内,干干净净,一根断草未留。”
文炜听知,惊魂千里,跑至朱昱灵前,两手抱住棺木,拚命的大哭,情甚凄惨。哭了好半晌,老僧拉开说道:“我此刻才明白了,令兄真是普天下情理以外人。可趁他走还未远,速到县中,哭诉于老爷前,差三班头役,星夜追拿这不孝不友的蠢才,将他私囊夺尽,着你押灵回乡。把他锁禁在监中,三年后放他出来,以泄公愤。二公子也不必回避出首胞兄声名,一个没天良、没伦理的人,与禽兽何殊?我是日夜效法佛爷爷的人,今日着你这一哭,不由的大动了肝火。你可照我话速行。”
朱文炜听了,一言不答,流着两行痛泪,走出庙去。老和尚见文炜软弱,气的只是摇头。
文炜回到寓所,与段诚哭诉,段诚笑道:“他这一走,我心里早打算的透熟。我不怕得罪主人,一个人中猪狗,再不必较论了。刻下身边还有几两银子,也可盘搅几日。即一文没有,老主人在此做官一场,不无情面。况相公帮助林公子,人人都号为义举。目今大相公席卷回乡,抛弃父骨,赶逐胞弟,通国切齿。刻下生者死者,从此不得回家,可再烦人出个捐单,也不愁百十两到手。况又有本县老爷,自必格外可怜。相公快写禀帖启知本县。我明早去寻老主人素好朋友,再烦劳他们举行。回得家乡,就好计较了,哭他气他何益?”
文炜恐扬兄之恶,不写禀帖,不意县中早已知道,差人送了两石仓米、四两银子,又将几个走动衙门好管事的绅士,面托与文炜设法,众绅士满口应承下来。谁料文炜走了否运,只三四天,便将县官因公挂误,新署印官漠不相关。地方绅士,实心好善者有几个?见县官一坏,便互相推诿起来。又得新典史念前后同官分上,自己捐了十两,又代请原上捐人。如此鬼弄了月余,仅捐了三十多两,共得银四十三两有奇,一总交付文炜谢责。
文炜与段诚打算,回家盘费有了,若扶灵,还差着百金。
段诚又想出一策,打听出崇宁县县官周曰谟,系河南睢州人,着文炜写哀怜手本,历诉困苦,他推念同乡,自必加倍照拂。
文炜亦以为然。又恐将捐银遗失,主仆相商,交与慈源寺老和尚。身边还有几两银子,各买了旧棉衣裤鞋袜等类,以便过冬出门。正要起身,岂期运败之人,随处坎坷,交与老和尚捐银,又被他徒弟法空盗窃逃去。主仆悔恨欲死,呈控在本县,县中批了捕厅。捕厅大怒,将老和尚严行责处。细问几次,委不知情,他又无力赔补。受刑不过,便行自缢,亏得段诚救免,文炜反替他在捕厅前讨情。金堂县亦再难开口,只得到崇宁县去,向管宅门人哭诉情由。宅门人甚是动怜,立即回禀本官。少刻出来,蹙着眉头道:“你的禀帖,他看过了,说你是远方游棍,在他治下假充乡亲,招摇撞骗,还要立即坐堂审你。亏得我再四开说,才吩咐值日头,把你逐出境外。你苦苦的投奔到此,我送你一千大钱做盘费,快回去罢。倘被他查知,大有不便。”
文炜含泪拜谢,拿了一千钱出来。
文炜与段诚相商,若再回金堂县,实无面目,打算着成都是省城地方,各处人俱有,或者有个际遇,亦未敢定。于是主仆奔赴成都,寻了个店住下。举目认不得一个人,况他二人住的店,皆往来肩挑背负之人,这“际遇”二字从何处说起?每天到出着二十个房钱,日日现要。从十月住至十一月尽间,盘费也告尽了,因拖欠下两日房钱,店东便出许多恶语。段诚见不是路,于城外东门二里地远,寻下个没香火的破庙,虽然寒冷,却无人要钱。又苦挨了几天,受不得饥饿,开首是段诚讨饭孝顺主人,竟不足两人吃用,次后文炜也只得走这条道路,这话不表。
再说朱文魁,弃绝了兄弟并他父灵柩,带了重资,欣喜回家。入得门,一家男妇俱来看问,见他穿着孝服,各大惊慌。
文魁走入内堂,便放声大哭,说父亲病故了。一家儿皆喊叫起来。哭罢,欧阳氏问道:“二相公和我家男人,想是在后面押灵。”
文魁又大哭道:“老相公做了三年官,除一个钱没弄下,到欠下人许多债负,灵柩不能回家。二相公同你男人去灌县上捐,不意遭风,主仆同死在川江。我一路和讨吃的一样,奔到家乡。”
话未说完,姜氏便痛倒在地。殷氏同欧阳氏将他扶入后院房中,劝解了一番,回到前边,与文魁洗尘接风。
姜氏直哭到上灯时候还不住歇,至定更以后,欧阳氏走来说道:“二主母且不必哭,我适才在外院夹道内,见隔壁李家叔侄同李必寿,从厅院外抬入两个大驮子,到大主母窗外,看来极其沉重,还有几个皮箱在上面。一个个神头鬼脸,偷着拆取,俱被李必寿同大相公搬移在房内,方才散去。大相公说老主人欠人多少债负,他一路和讨吃花子一般。既穷困至此,这些行李都是那里来的?从午后到家,此刻一更已过,才抬入来,先时在谁家寄放?以我看来,其中必大有隐情。我今晚一夜不睡,在他后面窗外听个下落,我此刻就去了。你安歇了罢,不必等我。”
到四更将尽,欧阳氏推门入来,见姜氏还坐在床头,对灯流涕,笑说道:“不用哭了,我听了个心满意足,此时他两口子都睡熟,我才来。”
遂坐在一边,将文魁夫妻前后话,细细的说了一遍,又骂道:“天地间,那有这样一对丧心的猎狗。”
姜氏道:“如此看来,二相公同你男人还在,老主人身死是实。只是他两人止有十两银子,能过得几日?该如何回家。”说罢,又流下泪来。
欧阳氏道:“不妨,二相公帮助姓林的,这是一件大善事,金堂县和新都县,自必人人通知。大相公此番弃抛父尸和弟,不消说,他这件大善事,也是两县通知的。何况老主人在那地方,大小做过个父母官,便是不相干人,遭逢此等事,地方上也有个评论,多少必有帮助,断断不至饿死。讨吃亦可回乡。”
又道:“大相公家赞美大相公有才情,有调度,也不枉他嫁夫一场。又说你是他们的祸根,必须打发了方可做事,早晚我即劝他嫁人。大相公说,这里的房产地土,须早些变卖,方好搬到山东,另立日月。总他二人有命回来,寻谁作对。大相公家道:你当日起身时,我曾嘱咐你,万一老杀才有个山高水低,就着你用这调虎离山,斩草除根之计。我还打算着得十年,不意天从人愿,只三年多就用上此计了。大相公又赞扬他是肚中有春秋的女人。”
姜氏:“他既无情,我亦无义。只可恨我娘家在山西地方,无人做主。我明日写一纸呈词,告在本县,求官府和他要人。”
欧阳氏道:“这使不得,我听的话,都是他夫妻暗昧话,算不得凭据,本县十分中有九分不准。即或信了我们的话,也得行文到四川查问,还不知四川官府当件事不当件事,到弄的他又生别计出来。依我的主见,他若是劝你改嫁,不可回煞了他,触他的恨怒,他又要另设别法。总以守过一二年然后改嫁回答他,用此缓军计,延挨的二相公回来就好了。从今后要步步防他们。就是我听得这些话,总包含在心里,面色口角间一点也不可显出,他若看出来,得祸更速。茶里饭里,到须小心,大相公家不先吃的东西,你千万不可先吃。只在此房消磨岁月,各项我自照管。”
姜氏道:“只怕他见你处处为护我,他先要除你,你也要留心。”
欧阳氏笑道:“我与二主母不同。他们若起了谋害我的意见,被我看出,我只用预备飞快短刀一把,于他两口子早起夜睡时,我就兑付他们了,总死不了两个,也着他死一个,有什么怕他处?”
从此过了月余。一日,殷氏收拾了酒菜到姜氏房内,与他消遣愁闷,两人叙谈闲话。殷氏道:“人生一世,犹如草生一秋。二兄弟死在川江,他的一生事体到算完结了。我又没三个两个儿子,与你夫妻承继,你又青春年少,日子比树叶儿还长,将来该作何了局?”
姜氏低头不语,殷氏又道:“我常听得和尚们放大施食,有两句话儿,说‘黄土埋不坚之骨,青史留虚假之名。’世上做忠臣节妇的,都是至愚至痴的人。我们做妇人的,有几分颜色,凭到谁家,不愁男人不爱。将来白头相守,儿女盈膝,这不是老来的受用。若说起目下同床共枕,知疼知痒,迟起早眠,相偎相抱的那一种恩情,以你这年纪算起,少说还有三十年风流。像你这样独守空房,灯残被冷,就是刮一阵风,下一阵雨,也觉得凄凄凉凉,无依无靠。再听上人些闲言离语,更是难堪。我是个口大舌长的人,没个说不出来的话。我和你在他这家中,六七年来也从没犯个面红,你素常也知道我的心肠最热。你若是起疑心,说是我为省衣服茶饭,撺掇你出门,我又不该说,这家中量你一人也省不下许多。你若把我这话当知心话,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定舍命访个青春俊俏郎君,还要他家道丰富,成就你下半世荣华。你若是看成放屁,我也不过长叹一声罢了。”
妻氏道:“嫂嫂的话,都是实意为我之言。只是我与他夫妻一场,不忍便去,待守过一二年孝服,那时再烦嫂嫂罢。”
殷氏道:“你原是玲珑剔透的人,一点就转。只是一年的话,还太远迂阔些,我过些时再与你从长计议。”
殷氏素常颇喜吃几杯酒,今见姜氏许了嫁人的话,心上快活,吃了二十来杯,方才别去。
正是:
弃绝同胞弟,妖婆意未宁。
又凭三寸舌,愚动烈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