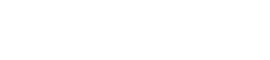第八十回
吴侍讲十年抚孤子 吕师相一疏苊名臣
这个姓吴的名学诚,为建文皇帝经筵日讲官司,素有品望。
帝出宫时扈从不及,恸哭数日,即欲自杀,又转一念道:“子在回何敢死?今间乘舆无恙,自当追求行在以图兴复。徒然一死,焉足塞责?”有传说者,言帝自吴入楚,将之滇中。吴侍讲遂弃其妻孥,止带一健仆,买个小渔舟,载了书籍,扮作渔翁,备了根钓竿,泛于长江之上。从九江入汉口,上三峡至于夔州。适又字帝在两粤,新华社记者折向洞庭,历潇湘,溯沅澧。又有说行在已在蜀中,复转而入沔阳,上夷陵,由涪江直抵册发源所在。往来转辗,终不得帝之踪迹。计欲舍舟就陆,求之道涂,又恐为人侦获,连性命都委之豺虎了。真是心上有个故君,梦寐中常在金阶玉殿之间。到得醒来,片叶孤舟,茫茫烟雾,能源奄酸?恸哭了几场,沈想了几次,忽自谓道:“有了。我听见说东就向东,说西就向西。不要说传闻不真,纵是真的,安知不君来臣去,臣来而君又去乎。我如今只在长江上下来往,天可怜见,少不得有见我帝主日子。”于是下及芜湖,上至灌口,往来游衍,逢人物色。取出所带书籍,看一本,随向江心掷一本,仰天痛哭一番。一日,在巴陵取《离骚》来读,是未经装订的,读一页,丢一页,又哭一番。适为贾舟附载文人听见,因此流传于世,野史上便说读的总是《离骚》,自比屈原不忘故主之意,这就是没见识的了。难道吴侍讲舟中所载尽是《离骚经》么?况且怀王是无道的,岂有将圣君比之之理?总是侍进愤懑已极,若始终求不着故主,也就要葬于江鱼之腹,留这书本何用,所以先付之江流。
一日泊舟在成都之皂江边,见有四五个童子钓鱼顽耍,内一个约十岁,嶷然坐着,虽形容憔悴,而眉目秀爽,又若有悲戚的光景。众童子都笑话他,他并不揪睬。侍讲心以为异,也就揽着自己的钓竿,移舟近前。一个童子拍手道:“那渔翁也是不会钓鱼的。”侍讲道:“还有谁不会钓鱼呢?”童子指着那嶷然坐的道:“是他。”侍讲便缓言问道:“童子今年几岁了?”旁一童答道:“他是野种,那里知道岁数。”侍讲又道:“他既不会钓,你们该教导他。”那坐着的童子答道:“我不要学钓鱼。”又一童子道:“他不要学钓鱼,要学的是讨饭。”侍讲见坐的童子含着悲酸,只不则声,就起了个恻隐之心,随问众童子:“他有父母么?”适有个老人走来,众童子共指道:“是他家里养着,不知那方流来的。”侍讲随步上涯,迎去施礼道:“多谢老丈厚德。”那老翁摸不着,便问渔翁:“你像个外方口气,从未相认,怎的谢我?”侍讲指着坐的童子道:“这是舍倒,失散已久,天幸今日遇见。闻知老丈收留,感激不浅。”就向腰间取出一包碎银,约有二两递与老翁道:“聊表微意,日后尚容补报。”老翁正为这童子一些生活不会做,倒要闲饭养他,虽然当日收留了,今却没摆布处,听了这话,笑逐颜开,便道:“既是令侄,竟领去罢,怎好要你的银子?”口中说着,手中接过去了。老翁随向童子道:“你们如今骨肉相逢,也不枉我养这两年。”童子不知所答。侍讲便道:“你今得随我回家,总是老翁收养之力。且到我船里去细说罢。”
看书者要知道这流落童子,若是住着安稳,怎肯随个渔翁?只因每日忍饥受冻,凌贱不过,一眼看着渔翁船里,堆着多少书籍,料不是个拐子,且离了这火坑再处,便立起身来,撇却钓竿,扯着渔翁的衣袂。侍讲随携了他的手,同向老翁作揖致谢,即别了下船而行。童子偷眼相一相渔翁的脸儿,又睃睃舱内的书籍,微微的叹了口气。吴侍讲问童子:“你为恁叹气?有话说与我。”童子道:“我从幼没了父母,不曾上学读书。如今见了这多少书本,因此叹气。”就呜呜咽呖的哭将起来。
侍讲见童子说话,大有志向,道:“你且勿哭,我正要问话。你父亲叫什么姓名?几时没有的?怎样流落在这边?”童子气噎不能答,捶胸大恸。侍讲已猜个八分,乃抚背而劝,方应道:“我父亲叫做胡子义,做的兵备道,还有个伯父,是朝中的大官。不知怎样京里乱将起来。伯父一家都被杀了,我父亲闻知,就丢了一家人口,只带着我弟兄,连夜逃出衙门,到这里一个王府内住了几时。听说要来追拿,又逃到一个山内。我父亲向着天说道:‘吾兄无子,天若不绝吾姓,自有好人收留。’黑夜里竟自去了。那时哥哥七岁,我只六岁,遇着这个老翁,收了我去,也不知哥哥怎么样了,也不知我母亲怎么样死了。”说罢又放声痛哭。侍讲触着心事,也自捶胸大恸连仆人也挥泪不已。
童子见渔翁哭得甚苦,道是因他起见,倒住了声。侍讲道:“噫,正是流泪眼相看流泪眼,断肠人说与断肠人。童子,适才我见你在难中,动了恻隐之心,提拔你的,也不知是忠臣的孤子。我对你说,我不是渔翁,我是建文皇帝朝中侍讲官。你的伯父胡子昭,做刑部侍郎,与我是意气之交。你的父亲做湖广荆门道,我亦曾会过。”说未毕,童子遽然拜道:“是我的父辈。这个大恩如何可报?愿认为父亲,教训孩儿罢。”侍讲道:“论理是年家子侄,也还不错。但宗祧为重,汝但呼我为父,我认汝为儿,姓是改不得的。”童子又拜过,才立起来问道:“孩儿这几年上,略闻得燕王夺了建文皇帝的天下,说杀了多少忠臣。我揣伯父、父亲,也为这个缘故,其实尚未详悉,求父亲大人示与孩儿。”侍讲就把燕王起兵,至建文逊国,杀戮忠臣义士情由,略说一遍。又道:“你伯父是方孝孺的至交,全家受戮的。临刑有诗曰:‘两间正气归泉壤,一点丹心在帝乡。’我至今记着。后闻得汝父亲避在蜀主府中。到弃汝弟兄逃去,我就不知道了。”童子又悲泣道:“若如此,我母亲一家子,都是被害的了。所以父亲也顾不得我弟兄二人。咳!这样大仇,怎生得报?”侍讲道:“这些话,不愧为子昭、子义的后人。我今为汝取个名字,叫胡复,是《易经》上的卦名。复字的解说,是六阴尽而一阳来复,在地正气初复之候,以寓建文圣主将来复国之意。在汝本身上讲,复君仇,复父仇,复祖宗旧德,复乡国故业,总含蓄在里面。”童子道:“孩儿不识个字,怎能如得父亲命名之意?还求父亲做主。”侍讲喟然叹道:“你还不知,我为要求建文皇帝,所以借此形藏。若求得着时,君臣生死一处;若求不着时,这大江中便是我葬身之所。到那时候,也顾不得你了。”童子道:“我随着父亲生死一处,也还得个好名目,强如死在别处。”侍讲道:“这不是我看之意。譬如我也弃了儿子来的,只为祖宗之香火,不可泯灭,岂有教汝同死之理,以绝胡姓之宗祧。且到其间,自然生出机会。你如今正是读书时候,幸亏得五经四书尚未投诸江流,我当一教汝。”便检出本《鲁论》来。胡复接在手中,颇识得几个字。侍讲道:“汝未上学,怎又识字?”胡复道:“孩儿三四岁上,母亲曾教我识字,至今还记得。”
侍讲从此教他读起书来,天资颖悟,殊不费力,一两年读完四书,又读五经,与他讲论都能闻一知二。不两年文章也做成了。吴侍讲有了这个伴儿,常常讲书论文,倒觉日子易过。
沸沸扬扬的,听得江舟上都传说圣姑娘娘已得了淮扬地方,如今就要取南京,永乐皇帝有些做不成了。又有个说倒不见渡江,已经取了庐州府,要杀到河南哩。胡复问侍讲:“是恁么圣姑娘娘?因何与燕贼作难,这其间有个机会否?”侍讲应道:“是一女流,仗有妖术,借着我君的年号,哄动人心,大抵是假公济私的。前者张天师在南都,曾斩他一个妖人,乃是马猴儿,即此可知。近来无识之徒多被煽惑。我们不用睬他。”
过了几时,舟从三峡而下,轰传湖广全省皆失,关老爷显圣,斩了荆州都督。因这位吕军师,是诸葛亮转世,所以关老爷助他哩。吴侍讲听了别的话不打紧,只关公显圣一语,大为奇异,心中暗想:“若不是正气之人,关侯焉得助他?”遂谓胡复道:“荆州已得,天下摇动。要复建文担子,却在我身上。我欲去察他动静,若是借此为名,欲劫我主,如曹瞒之劫汉献帝的,我便将段实之笏,击碎他的贼脑,比死于江中,更为显荣了。”胡复道:“大人作何去见他?”侍讲道:“儒衣儒冠,是我的初服,谒见故主要用的,所以带在这里。到他辕门口,自有随机应变之法。”就取出来穿戴了,一径上岸入城,寻到帅府。
目今谒贵是件大难的事,秀才们拿着禀揭,满面堆笑,倩求传递。那些衙役总不来睬的。吕军师任兼将相,掌握着大兵权。吴侍讲破巾敝衫,又不具个名柬,如何可以会面?那知吕军师好贤礼士,有周公握发吐哺之风,不论何人,到辕即传。那时侍讲故意轻忽,说要见你们军师,司阍的登时传报请进。军师望见是个儒者,而行步有大臣气象,即降阶延接。侍讲已尽折了一半。一揖升堂,向军师道:“大人上座,容儒生拜见。”军师笑道:“学生非富贵中人,先生休得过谦,只行常礼。”侍讲乃再揖再逊,然后就客位而坐。牢师请教姓名,应曰:“小儒何足挂齿。请问大人,关侯显圣有之乎?”军师举手答道:“诚有之。神武乃上为国家,非为学生也。”又问:“大人以片旗一语,而服荆楚亿兆之心,有之乎?”应曰:“此小智耳,无关于大体。”侍讲亦举手曰:“荆州东连吴会,西控巴蜀,北抵中原,南极衡湘,为天下之枢机,可以莅中国而朝四夷。儒生不才,愿备指使。”军师笑道:“我帝师乃上界金仙,其视荣华点染,不啻污及巢父之犊。今日而建文复位,则此刻归于蓬岛。所为的培植天伦,扶养正气,诛奸逆于强盛,挽忠义于沦亡,躬行《春秋》之法,以昭大义于万世。微独帝师,即学生一待圣驾回銮,完此心事,亦遂逍遥乎物表。所以兵下河南,三过家门不入。”
言未既,吴侍讲遽拜于地曰:“噫,我何知而敢测命世之大贤哉?”军师忙答礼,相扶而起。侍讲道:“学生有罪,当日原备员经筵。”军师曰:“得非泛舟之吴学诚先生乎?”侍讲曰:“然。十四五年,不知行在之所。今者军师笃爱吾君,学生即当遍天下而求之。求而不获,亦不复返。愿军师代为转奏。”
军师对曰:“不然。吴门史彬、浦江郑洽,俱知帝之得在。前岁有方外祭酒钱芹,约彼二公同往,迎请回銮,当亦不远。纵使圣驾又幸他处,三公自能踪迹,无烦跋涉。学生愚意,先请先生入朝,端百揆而在工,使天下之人,咸知吴侍讲入朝为相,则我君之复位有日。所以系社稷之重,而慰苍黎之望,非独区区好贤之私也。”侍讲曰:“帝未复位,而臣子先膺爵禄,可乎?”
军师曰:“不有臣子,焉得有君?臣子不先受爵,乌得称为行在?今日而无臣。是并无帝也。故居乱世而人之所属望,多决于名臣之去就。先生其勿固辞。”侍讲曰:“军师命之矣。舟中尚有一仆,并胡少司寇之孤子。”军师即传令请至,略询来由,下榻帅府。每谈往者行失,时相流涕。
一日,报关帝庙修整告竣,军师即约竺讲同去行香。礼毕,军师偶有所得,题诗于粉壁上云:
坐镇荆门控许都,心悬汉帝运将无。兴刘岂在西吞蜀,讨贼何须东结吴。
一卷《春秋》名自正,百年兄弟道犹孤。苍茫浩气归空后,太息三分小伯图。
吴侍讲大惊,赞道:“此千古法眼也。人但知关侯以浩然之气而成神,而不知所谓浩然者何在。愚意亦尝论之。蜀之臣子,其心皆为蜀而不为汉,为先主而不为献帝,诸葛且然,况其下者乎!蜀与汉原略有分别,晦庵以正统与之者,盖因献帝被废,势不得不以蜀为汉,而黜曹、吴之僭篡。若云以先主为中山靖王之后,可以,则西川之刘焉、刘璋、独非汉之宗室乎?何得扼其吭而夺之,拊其背而逐之哉!唯神武不与蜀事,坐镇荆州,以讨贼为己任,是其灭曹兴汉之心,为献帝非为先主也。即先主亦为献帝之臣,故可以兄事之,而不可以君事之。所谓‘一卷春秋名自正,百年兄弟道犹孤’也。武侯云‘东连孙吴,北拒曹操’,亦因先主孤穷之时,不得已而出此策。至于平曹之后,再议伐吴,未免所用者权术。若神武之视吴,与曹等耳。吴之割据,与曹之篡窃,易地皆然,断不可云彼善于此而与之连结。所云‘兴刘岂在西天蜀,讨贼何须东结吴’也。此所谓浩然之气之本也。先生今日之为建文,与关公同一心事,所以有此卓见。拜拜,服服!”军师固谦谢之。
随回帅府,手草五疏,一荐吴学诚先达名臣,宜膺师保之任,以副四海望治之心。一荐姚襄才器沈毅,文武兼优,宜令开府荆州,弹压敌境。又沈珂可任荆南监军道,董春秋可授荆北监军道之职。一荐俞如海为镇守德安将军。一言京营不可缺员,瞿雕儿、阿蛮儿等,仍令回京。唯刘超暂留臣所。请以郭开山代其缺,外齐卒一万,并令回京护卫,以遂其室家之思。一言比年以师旅饥馑,停科六载。今中原底定,吴楚怀来,皆愿观光。请于本年六科并举,以收人杰。遂设筵与侍讲饯行。吴学诚即携了胡复赴济南阙下。
去后数日,忽报方外祭酒钱芹回来复命,病在舟中。军师即令用暖舆舁进帅府。一面延医诊治,一面具疏报闻。请看名臣一出,四海倾心,义士三呼,千秋堕泪。下回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