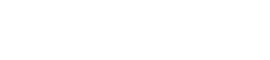第五十七回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 开封府包相保贤豪
且说白玉堂纵身上船,那船就是一晃,渔翁连忙用篙撑住,道:“客官好不晓事。此船乃捕鱼小船,俗名划子,你如何用猛力一趁。幸亏我用篙撑住;不然,连我也就翻下水去了。好生的荒唐呀!”白玉堂原有心事,恐被人追上,难以脱身;幸得此船肯渡,他虽然叨叨数落,却也毫不介意。那渔翁慢慢的摇起船来,撑到江心,却不动了。便发话道:“大清早起的,总要发个利市。再者俗语说的是,“船家不打过河钱”。客官有酒资拿出来,老汉方好渡你过去。”白玉堂道:“老丈,你只管渡我过去,我是不失信的。”渔翁道:“难,难,难,难!口说无凭,多少总要凭信的。”白玉堂暗道:“叵耐这厮可恶!偏我来的仓猝,并未带得银两。──也罢,且将我这件衬袄脱下给他。幸得里面还有一件旧衬袄,尚可遮体。候渡到那面,再作道理。”想罢,只得脱下衬袄,道:“老丈,此衣足可典当几贯钱钞,难道你还不凭信么?”渔翁接过抖开来,看道:“这件衣服,若是典当了,可以比捕鱼有些利息了。客官休怪,这是我们船家的规矩。”
正说间,忽见那边飞也似的赶了一只渔船来,口中说道:“好呀!清早发利市,见者有分。须要沽酒请我的。”说话间,船已临近。这边的渔翁道:“甚么大利市,不过是件衣服。你看看,可典多少钱钞?”说罢,便将衣服掷过。那渔人将衣服抖开一看,道:“别管典当多少,足彀你我喝酒了。老兄,你还不口头馋么?”渔翁道:“我正在思饮,咱们且吃酒去。”只听嗖的一声,已然跳到那边船上。那边渔人将篙一支,登时飞也似的去了。
白玉堂见他们去了,白白的失去衣服,无奈何,自己将篙拿起来撑船。可煞作怪,那船不往前走,只是在江心打转儿。不多会,白玉堂累得通身是汗,喘吁不止。自己发恨道:“当初与其练那独龙桥的,何不下工夫练这渔船呢?今日也不至于受他的气了。”正在抱怨,忽见小小舱内出来一人,头戴斗笠,猛将斗笠摘下,道:“五弟久违了!世上无有十全的人,也没有十全的事,你抱怨怎的?”白玉堂一看,却是蒋平,穿著水靠,不由得气冲宵汉,一声怪叫道:“嗳哟,好病夫!那个是你五弟?”蒋爷道:“哥哥是病夫,好称呼呀。这也罢了。──当初叫你练练船只,你总以为这没要紧,必要练那出奇的顽意儿。到如今,你那独龙桥那里去了?”白玉堂顺手就是一篙,蒋平他就顺手落下水去。白玉堂猛然醒悟,道:“不好,不好!他善识水性,我白玉堂必被他暗算。”两眼尽往水中注视。再将篙拨船时,动也不动,只急得他两手扎煞。
忽见蒋平露出头来,把住船边,道:“老五呀!你喝水不喝?”白玉堂未及答言,那船已然底儿朝天,把个锦毛鼠弄成水老鼠了。蒋平恐他过于喝多了水,不是当耍的,又恐他不喝一点儿水,也是难缠的;莫若叫他喝两三口水,趁他昏迷之际,将就着到了茉花村,就好说了。他左手揪住发绺,右手托定腿洼,两足踏水,不多时即到北岸,见有小船三四只在那里等候。这是蒋平临过河拆桥时,就吩咐下的。船上共有十数人,见蒋爷托定白玉堂,大家便嚷道:“来了,来了!四老爷成了功了!上这里来。”蒋爷来到切近,将白玉堂往上一举。众水手接过,便要控水。蒋爷道:“不消,不消。你们大家把五爷寒鸦赴水的背剪了,头面朝下,用木杠即刻抬至茉花村。赶到那里,大约五爷的水也控净了,就苏醒过来了。”众水手只得依命而行。七手八脚的捆了,用杠穿起,扯连扯连抬着个水淋淋的白玉堂,竟奔茉花村而来。
且说展熊飞同定卢方徐庆、兆兰兆蕙相陪,来到茉花村内。刚一进门,二爷便问伴当道:“蒋四爷可好些了?”伴当道:“蒋四爷于昨晚二员外起身之后,也就走了。”众人诧异,道:“往那里去了?”伴当道:“小人也曾问来,说:“四爷病着,往何方去呢?”四爷说:“你不知道,我这病是不要紧的;皆因有个约会等个人,却是极要紧的。”小人也不敢深问,因此四爷也就走了。”众人听了,心中纳闷,惟独卢爷着急,道:“他的约会,我焉有不知的?从来没提起过,好生令人不解。”丁大爷道:“大哥不用着急,且到厅上坐下,大家再作商量。”说话间,来到厅上。丁大爷先要去见丁母。众人俱言:“代为叱名请安。”展爷说:“俟事体消停,再去面见老母。”丁大爷一一领命,进内去了。丁二爷吩咐伴当:“快快去预备酒饭。我们俱是闹了一夜的了,又渴又饥。快些,快些!”伴当忙忙的传往厨房去了。少时,丁大爷出来,又一一的替老母问了众人的好。又向展爷道:“家母听见兄长来了,好生喜欢。言事情完了,还要见兄长呢。”展爷连连答应。早见伴当调开桌椅,安放杯箸。上面是卢方,其次展昭徐庆,兆兰兆蕙在主位相陪。
刚然入座,才待斟酒,忽见庄丁跑进来,禀道:“蒋老爷回来了,把白五爷抬来了。”众人听了,又是惊骇,又是欢喜,连忙离座出厅,俱各迎将出来。到了庄门,果见蒋四爷在那里吩咐,把五爷放下抽杠解缚。此时白玉堂已然吐出水来,虽然苏醒,尚不明白。卢方见他面目焦黄,浑身犹如水鸡儿一般,不觉泪下。展爷早赶步上前,将白玉堂扶着坐起,慢慢唤道:“五弟醒来,醒来。”不多时,只见白玉堂微睁二目。看了看展爷,复又闭上。半晌,方嘟嚷道:“好病夫呀!淹得我好!淹得我好!”说罢,哇的一声,又吐出许多清水,心内方才明白了。睁眼往左右一看,见展爷蹲在身旁,卢方在那里拭泪,惟独徐庆蒋平二人,一个是怒目横眉,一个是嬉皮笑脸。白玉堂看见蒋爷,便要挣扎起来,道:“好病夫呀!我是不能与你干休的。”展爷连忙扶住,道:“五弟且看愚兄薄面,此事始终皆由展昭而起。五弟如有责备,你就责备展昭就是了。”丁家弟兄连忙上前扶起玉堂,说道:“五弟且到厅上去沐浴更衣后,有甚么话再说不迟。”白玉堂低头一看,见浑身连泥带水好生难看,又搭着处处皆湿,遍体难受得很。到此时也没了法子了,只得说:“小弟从命。”
大家步入庄门,进了厅房。丁二爷叫小童掀起套间软帘,请白五爷进内。只见澡盆、堂布、香肥皂、胰子、香豆面。床上放着洋布汗遢中衣、月白洋绉套裤、靴、袜、绿花氅、月白衬袄、丝绦、大红绣花武生头巾,样样俱是新的。又见小童端了一磁盆热水来,放在盆架之上,请五爷坐了,打开发纂,先将发内泥土洗去,又换水添上香豆面洗了一回,然后用木梳通开,将发纂挽好,扎好网巾。又见进来一个小童,提着一桶热水注在澡盆之内,请五爷沐浴。两个小童就出来了,白玉堂即将湿衣脱去,坐在矮凳之上,周身洗了,用堂布擦干,穿了中衣等件。又见小童进来,换了热水,请五老爷净面。然后穿了衣服,戴了武生巾。其衣服靴帽尺寸长短,如同自己一样,心中甚为感激丁氏兄弟,只是恼恨蒋平,心中忿忿。
只见丁二爷进来,道:“五弟沐浴已毕,请到堂屋中谈话饮酒。”白玉堂只得随出,见他仍是怒容满面。卢方等立起身来说:“五弟,这边坐,叙话。”玉堂也不言语。见方才之人皆在,惟不见蒋二爷,心中纳闷。只见丁二爷吩咐伴当摆酒。片时工夫,已摆得齐整,皆是美味佳肴。丁大爷擎杯,丁二爷执壶,道:“五弟想已饿了,且吃一杯暖一暖寒气。”说罢,斟上酒来,向玉堂说:“五弟请用。”白玉堂此时欲不饮此酒,怎奈腹中饥饿,不作脸的肚子咕噜噜的乱响,只得接杯一饮而尽。又斟了门杯。又给卢爷展爷徐爷斟了酒。大家入座。
卢爷道:“五弟,已往之事,一概不必提了。无论谁的不是,皆是愚兄的不是。惟求五弟同到开封府,就是给为兄的作了脸了。”白玉堂闻听,气冲斗牛,不好向卢方发作,只得说:“叫我上开封府,万万不能。”展爷在旁插言道:“五弟不要如此,凡事必须三思而后行,还是大哥所言不差。”玉堂道:“我管甚么“三思”、“四思”,横竖我不上开封府去。”
展爷听了白玉堂之言,有许多的话要问他,又恐他有不顺情理之言,还是与他闹是不闹呢?正在思想之际,忽见蒋爷进来,说:“姓白的,你别过于任性了。当初你向展兄言明盗回三宝,你就同他到开封府去;如今三宝取回,就该同他前往才是。即或你不肯同他前往,也该以情理相求。为何竟自逃走?不想又遇见我救了你的性命,又亏了丁兄给你换了衣服,如此看待,为的是成全朋友的义气。你如今不到开封府,不但失信于展兄,而且对不住丁家兄弟。你义气何在?”白玉堂听了,气得喊叫如雷,说:“好病夫呀!我与你势不两立了!”站起来,就奔蒋爷拚命。丁家兄弟连忙上前拦住,道:“五弟不可,有话慢说。”蒋爷笑道:“老五呀,我不与你打架。就是你打我,我也不还手。打死我,你给我偿命。我早已知道你是没见过大世面的,如今听你所说之言,真是没见过大世面。”白玉堂道:“你说,我没见过大世面。你倒要说说我听。”
蒋爷笑道:“你愿听,我就说与你听。你说你到过皇宫内院,忠义祠题诗,万代寿山前杀命,奏折内夹带字条,大闹庞府杀了侍妾。你说这都是人所不能的。这原算不了奇特,这不过是你仗着有飞檐走壁之能,黑夜里无人看见,就遇见了皆是没本领之人。这如何算得是大干呢?如何算得见过大世面呢?如若是见过世面,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中,瞻仰过包相爷半堂问事,那一番的威严令人可畏。未升堂之时,先是有名头的皂班、各项捕快、各项的刑具、各班的皂役,一班一班的由角门而进,将铁链夹棍各样刑具往堂上一放。又有王马张赵将御铡请出。喊了堂威,左右排班侍立。相爷由屏风后步入公堂。那一番赤胆忠心为国为民一派的正气,姓白的,你见了也就威风顿减。这些话彷佛我薄你。皆因你所为之事都是黑夜之间,人皆睡着,由着你的性儿,该杀的就杀,该偷的就偷拿了走了。若在白昼之间,这样事全是不能行的。我说你没见过大世面,所以不敢上开封府去,就是这个缘故。”
白玉堂不知蒋爷用的是激将法,气得他三尸神暴出,五陵豪气飞空,说:“好病夫!你把白某看作何等样人?慢说是开封府,就是刀山箭林,也是要走走的。”蒋爷笑嬉嬉道:“老五哇,这是你的真话呀?还是仗着胆子说的呢?”玉堂嚷道:“这也算不了甚么大事,也不便与你撒谎。”蒋爷道:“你既愿意去,我还有话问你。这一起身虽则同行,你万一故意落在后头,我们可不能等你。你若逃了,我们可不能找你。还有一件事更要说明:你在皇宫内院干的事情,这个罪名非同小可。到了开封府,见了相爷,必须小心谨慎,听包相爷的钓谕,才是大丈夫所为。若是你仗着自己有飞檐走壁之能,血气之勇,不知规矩,口出胡言大话,就算不了行侠尚义英雄好汉,就是个浑小子,也就不必上开封府去了。你就请罢!再也不必出头露面了。”白玉堂是个心高气傲之人,如何能受得这些激发之言,说:“病夫,如今我也不合你论长论短。俟到了开封府,叫你看看白某是见过大世面,还是没有见过大世面,那时再与你算帐便了。”蒋爷笑道:“结咧!看你的好好劲儿了。好小子!敢作敢当,才是好汉呢。”兆兰等恐他二人说翻了,连忙说道:“放着酒不吃,说这些不要紧的话作甚么呢?”丁大爷斟了一杯酒,递给玉堂;丁二爷斟了一杯酒,递给蒋平,二人一饮而尽。然后大家归座,又说了些闲话。
白玉堂向着蒋爷道:“我与你有何仇何恨?将我翻下水去,是何缘故?”蒋爷道:“五弟,你说话太不公道。你想想你作的事那一样儿不利害,那一样儿留情份,甚至说话都叫人磨不开。就是今日,难道不是你先将我一篙打下水去么?幸亏我识水性;不然,我就淹死了。怎么你倒恼我?我不冤死了么?”说得众人都笑起来了。丁二爷道:“既往之事,不必再说。莫若大家喝一回,吃了饭,也该歇息歇息了。”说罢,才要斟酒。
展爷道:“二位贤弟且慢,愚兄有个道理。”说罢,接过杯来,斟了一杯,向玉堂道:“五弟,此事皆因愚兄而起。其中却有分别。今日当着众位仁兄贤弟俱各在此,小弟说一句公平话,这件事实系五弟性傲之故,所以生出这些事来。如今五弟既愿到开封府去,无论何事,我展昭与五弟荣辱共之。如五弟信的,就饮此一杯。”大家俱称赞道:“展兄言简意深,真正痛快。”白玉堂接杯一饮而尽,道:“展大哥,小弟与兄台本无仇隙,原是义气相投的。诚然是小弟少年无知不服气的起见。如到开封府,自有小弟招承,断不累及吾兄。再者,小弟屡屡唐突冒昧,蒙兄长的海涵,小弟也要敬一杯,陪个礼才是。”说罢,斟了一杯,递将过来。大家说道:“理当如此。”展爷连忙接过,一饮而尽,复又斟上一杯,道:“五弟既不挂怀劣兄。五弟与蒋四兄也要对敬一杯。”蒋爷道:“甚是,甚是。”二人站起来,对敬了一杯。众人俱各大乐不止。然后归座,依然是兆兰兆蕙斟了门杯,彼此畅饮。又说了一回本地风光的事体,到了开封府应当如何的光景。
酒饭已毕,外面已备办停当。展爷进内与丁母请安禀辞,临别留下一封谢柬,是给松江知府的,求丁家弟兄派人投递。丁大爷丁二爷送至庄外,眼看着五位英雄带领着伴当数人,蜂拥去了。一路无话。
及至到了开封府,展爷便先见公孙策商议,求包相保奏白玉堂;然后又与王马张赵彼此见了。众人见白玉堂少年英雄,无不羡爱。白玉堂到此时也就循规蹈矩,诸事仗卢大爷提拨。
展爷与公孙先生来到书房,见了包相,行参已毕,将三宝呈上。包公便吩咐李才送到后面收了。展爷便将自己如何被擒,多亏茉花村双侠打救,又如何蒋平装病悄地拿获白玉堂的话,说了一遍;惟求相爷在圣上面前递折保奏。包公一一应允,也不升堂,便叫将白玉堂带到书房一见。展爷忙到公所道:“相爷请五弟书房相见。”白玉堂站起身来就要走,蒋平上前拦住,道:“五弟且慢,你与相爷是亲戚,是朋友?”玉堂道:“俱各不是。”蒋爷道:“既无亲故,你身犯何罪,就是这样见相爷,恐于理上说不去。”白玉堂猛然省悟,道:“亏得四哥提拨,险些儿误了大事。”
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