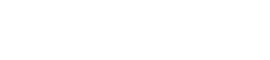唐纪十一
起强圉作噩五月,尽上章困敦,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上
◎ 贞观十一年丁酉,公元六三七年
五月,壬申,魏征上疏,以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薨。彦博久掌机务,知无不为。上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精神耗竭,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安逸,竟夭天年!”
丁巳,上幸明德宫。
己未,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世袭。戊辰,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非有大故,无得黜免。己巳,徙许王元祥为江王。
秋,七月,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阳宫,坏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馀人。
魏征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馀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乙未,车驾还洛阳,诏:“洛阳宫为水所毁者,少加修缮,才令可居。自外众材,给城中坏庐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征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馀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向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夫昧爽丕显,后世犹怠,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馀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馀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陛下宠遇诸王,颇有过厚者,万代之后,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诸王,但无缧绁耳。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冬,十月,癸丑,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上猎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对曰:“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寻加光禄大夫。
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上曰:“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面折我?”对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上悦。
十一月,辛卯,上幸怀州;丙午,还洛阳宫。
故荆州都督武士彟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
◎ 贞观十二年戊戌,公元六三八年
春,正月,乙未,礼部尚书王珪奏:“三品已上遇亲王于路皆降乘,非礼。”上曰:“卿辈苟自崇贵,轻我诸子。”特进魏征曰:“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为王降乘,诚非所宜当。”上曰:“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对曰:“自周以来,皆子孙相继,不立兄弟,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此为国者所深戒也。”上乃从珪奏。
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葇、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恶之,命士廉等遍责天下谱谍,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分为九等。士廉等以黄门侍郎崔民幹为第一。上曰:“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卬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与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幹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
二月,乙卯,车驾西还;癸亥,幸河北,观砥柱。
甲子,巫州獠反,夔州都督齐善行败之,俘男女三千馀口。
乙丑,上祀禹庙。丁卯,至柳谷,观盐池。庚午,至蒲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车驾,盛饰廨舍楼观,又饲羊百馀口、鱼数百头以馈贵戚。上数之曰:“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须,皆资库物。卿所为乃亡隋之弊俗也。”甲戌,幸长春宫。
戊寅,诏曰:“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风劲草,实表岁寒之心;可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
闰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丁未,车驾至京师。
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丙子,以皇孙生,宴五品以上于东宫。上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征之功也。”皆赐之佩刀。上谓征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对曰:“威德所加,比贞观之初则远矣;人悦服则不逮也。”上曰:“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对曰:“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为,犹往年也,何以异?”对曰:“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上曰:“其事可闻欤?”对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云:‘赏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资,陛下欲诛之,纳戴胄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壬申,弘文馆学士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卒,上哭之恸。世南外和柔而内忠直,上尝称世南有五绝: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学,四文辞,五书翰。
秋,七月,癸酉,以吏部尚书高士廉为右仆射。
乙亥,吐蕃寇弘州。
八月,霸州山獠反,烧杀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馀家。
初,上遣使者冯德遐抚慰吐蕃,吐蕃闻突厥、吐谷浑皆尚公主,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上未之许。使者还,言于赞普弃宗弄赞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许尚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相离间,唐礼遂衰,亦不许婚。”弄赞遂发兵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北,民畜多为吐蕃所掠。
吐蕃进破党项、白兰诸羌,帅众二十馀万屯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寻进攻松州,败都督韩威;羌酋阎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连兵不息,其大臣谏不听而自缢者凡八辈。壬寅,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甲辰,以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督步骑五万击之。
吐蕃攻城十馀日,进达为先锋,九月,辛亥,掩其不备,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斩首千馀级。弄赞惧,引兵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上许之。
甲寅,上问侍臣:“帝王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初,突厥颉利既亡,北方空虚,薛延陀真珠可汗帅其部落建庭于都尉犍山北、独逻水南,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拔酌、颉利苾主南、北部。上以其强盛,恐后难制,癸亥,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
冬,十月,乙亥,巴州獠反。
己卯,畋于始平;乙未,还京师。
钧州獠反;遣桂州都督张宝德讨平之。十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营飞骑于玄武门,以诸将军领之。又简飞骑才力骁健、善骑射者,号百骑,衣五色袍,乘骏马,以虎皮为鞯,凡游幸则从焉。
己巳,明州獠反;遣交州都督李道彦讨平之。
十二月,辛巳,左武候将军上官怀仁击反獠于壁州,大破之,虏男女万馀口。
是岁,以给事中马周为中书舍人。周有机辩,中书侍郎岑文本常称:“马君论事,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烦,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
霍王元轨好读书,恭谨自守,举措不妄。为徐州刺史,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人问玄平王所长,玄平曰:“无长。”问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所短乃见所长,至于霍王,无所短,吾何以称其长哉!”
初,西突厥咥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仍各赐一箭,谓之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置五大啜,居碎叶以东;右厢号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居碎叶以西;通谓之十姓。咥利失失众心,为其臣统吐屯所袭。咥利失兵败,与其弟步利设走保焉耆。统吐屯等将立欲谷设为大可汁,会统吐屯为人所杀,欲谷设兵亦败,咥利失复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设为乙毘咄陆可汗。乙毘咄陆既立,与咥利失大战,杀伤甚众。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属乙咄陆,以东属咥利失。
处月、处密与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
◎ 贞观十三年己亥,公元六三九年
春,正月,乙巳,车驾谒献陵;丁未,还宫。
戊午,加左仆射房玄龄太子少师。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男遗爱尚上女高阳公主,女为韩王妃,深畏满盈,上表请解机务;上不许。玄龄固请不已,诏断表,乃就职。太子欲拜玄龄,设仪卫待之,玄龄不敢谒见而归,时人美其有让。玄龄以度支系天下利害,尝有阙,求其人未得,乃自领之。
礼部尚书永宁懿公王珪薨。珪性宽裕,自奉养甚薄。于今,三品已上皆立家庙,珪通贵已久,独祭于寝。为法司所劾,上不问,命有司为之立庙以愧之。
二月,庚辰,以光禄大夫尉迟敬德为鄜州都督。
上尝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馀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为之流涕,曰:“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邪!”
上又尝谓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头谢曰:“臣妻虽鄙陋,相与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上乃止。
戊戌,尚书奏:“近世掖庭之选,或微贱之族,礼训蔑闻;或刑戮之家,忧怨所积。请自今后宫及东宫内职有阙,皆选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礼聘纳;其没官口及素微贱之人,皆不得补用。”上从之。
上既诏宗室群臣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侍御史马周亦上疏,以为:“尧、舜之父,犹有硃、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正欲留之也,而栾黡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
会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皆不愿之国,上表固让,称:“承恩以来,形影相吊,若履春冰;宗戚忧虞,如置汤火。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协事宜,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且后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宪,自取诛夷,更因延世之赏,致成剿绝之祸,良可哀愍。愿停涣汗之旨,赐其性命之恩。”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辅朕子孙,共传永久;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诏停世封刺史。
高昌王麹文泰多遏绝西域朝贡,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上下书切责,征其大臣阿史那矩,欲与议事,文泰不遣,遣其长史麹雍来谢罪。颉利之亡也,中国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诏文泰归之,文泰蔽匿不遣。又与西突厥共击破焉耆,焉耆诉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问状,且谓其使者曰:“高昌数年以来,朝贡脱略,无籓臣礼,所置官号,皆准天朝,筑城掘沟,预备攻讨。我使者至彼,文泰语之云:‘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谓薛延陀云:‘既为可汗,则与天子匹敌,何为拜其使者!’事人无礼,又间邻国,为恶不诛,善何以劝!明年当发兵击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报,请发所部为军导以击高昌。”上遣民部尚书唐俭、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赍缯帛赐薛延陀,与谋进取。
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宫。
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从突利入朝,历位中郎将。居家无赖,怨突利斥之,乃诬告其谋反,上由是薄之,久不进秩。结社率阴结故部落,得四十馀人,谋因晋王治四鼓出宫,开门辟仗,驰入宫门,直指御帐,可有大功。甲申,拥突利之子贺逻鹘夜伏于宫外,会大风,晋王未出,结社率恐晓,遂犯行宫,逾四重幕,弓矢乱发,卫士死者数十人。折冲孙武开等帅众奋击,久之,乃退,驰入御厩,盗马二十馀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获,斩之,原贺逻鹘投于岭表。
庚寅,遣武候将军上官怀仁击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虏男女六千馀口。
五月,旱。甲寅,诏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征上疏,以为:“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其间一条以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上深加奖叹,云:“已列诸屏障,朝夕瞻仰,并录付史官。”仍赐征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柯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蛮、俚降者二万八千馀户。
丙申,立皇弟元婴为滕王。
自结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诏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籓屏,长保边塞。突厥咸惮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农卿郭嗣本赐薛延陀玺书,言“颉利既败,其部落咸来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后善,待其达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于河南,任其畜牧。今户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薛延陀奉诏。于是遣思摩帅所部建牙于河北,上御齐政殿饯之,思摩涕泣,奉觞上寿曰:“奴等破亡之馀,分为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复立为可汗,愿万世子孙恒事陛下。”又遣礼部尚书赵郡王孝恭等赍册书,就其种落,筑坛于河上而立之。上谓侍臣曰:“中国,根幹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幹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朕不用魏征言,几致狼狈。”又以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熟为右贤王。忠,苏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怀慕中国,见使者必泣涕请入侍;诏许之。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诏以“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比来诉讼者或自毁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后依法。”
冬,十月,甲申,车驾还京师。
十一月,辛亥,以侍中杨师道为中书令。
戊辰,尚书左丞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
上犹冀高昌王文泰悔过,复下玺书,示以祸福,征之入朝;文泰竟称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等将兵击之。
乙亥,立皇子福为赵王。
己丑,吐谷浑王诺曷钵来朝,以宗女为弘化公主,妻之。
壬辰,上畋于咸阳,癸巳,还宫。
太子承乾颇以游畋废学,右庶子张玄素谏,不听。
是岁,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一十一。
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病,不呼医饵药。有僧自西域来,善咒术,能令人立死,复咒之使苏。上择飞骑中壮者试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干正,请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若为物所击,遂不复苏。又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长安士女辐凑如市。奕时卧疾,谓其子曰:“吾闻有金刚石者,性至坚,物莫能伤,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试焉。”其子往见佛齿,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时年八十五。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西突厥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发与乙毘咄陆可汗通谋作乱,咥利失穷蹙,逃奔汗而死。弩失毕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为乙毘沙钵罗叶护可汗。沙钵罗叶护既立,建庭于虽合水北,谓之南庭,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附之。咄陆建牙于镞曷山西,谓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燖、触水昆等国皆附之,以伊列水为境。
◎ 贞观十四年庚子,公元六四零年
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长安系囚大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赋,赐泰府僚属及同里老人有差。
二月,丁丑,上幸国子监,观释奠,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赐祭酒以下至诸生高第帛有差。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经已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馀人。上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
壬午,上幸骊山温汤;辛卯,还宫。
乙未,诏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子孙以闻,当加引擢。
三月,窦州道行军总管党仁弘击罗窦反獠,破之,俘七千馀口。
辛丑,流鬼国遣使入贡。去京师万五千里,滨于北海,南邻靺鞨,未尝通中国,重三译而来。上以其使者佘志为骑都尉。
丙辰,置宁朔大使以护突厥。
夏,五月,壬寅,徙燕王灵夔为鲁王。
上将幸洛阳,命将作大匠阎立德行清暑之地。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宫于汝州西山。立德,立本之兄也。
高昌王文泰闻唐兵起,谓其国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已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及闻唐兵临碛口,忧惧不知所为,发疾卒,子智盛立。
军至柳谷,诇者言文泰刻日将葬,国人咸集于彼,诸将请袭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无礼,故使吾讨之,今袭人于墟墓之间,非问罪之师也。”于是鼓行而进,至田城,谕之,不下,诘朝攻之,及午而克,虏男女七千馀口。以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夜,趋其都城,高昌逆战而败,大军继至,抵其城下。
智盛致书于君集曰:“得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天罚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袭位未几,惟尚书怜察。”君集报曰:“苟能悔过,当束手军门。”智盛犹不出。君集命填堑攻之,飞石雨下,城中人皆室处。又为巢车,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飞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与西突厥可汗相结,约有急相助;可汗遣其叶护屯可汗浮图城,为文泰声援。及君集至,可汗惧而西走千馀里,叶护以城降。智盛穷蹙,癸酉,开门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一万七千七百,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上欲以高昌为州县,魏征谏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妇首来朝,其后稍骄倨,故王诛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抚其百姓,存其社稷,复立其子,则威德被于遐荒,四夷皆悦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馀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臣未见其可。”上不从,九月,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各置属县,乙卯,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
君集虏高昌王智盛及其群臣豪杰而还。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
侯君集之讨高昌也,遣使约焉耆与之合势,焉耆喜,听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诣军门谒见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为高昌所夺,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归之。
冬,十月,甲戌,荆王元景等复表请封禅,上不许。
初,陈仓折冲都尉鲁宁坐事系狱,自恃高班,慢骂陈仓尉尉氏刘仁轨,仁轨杖杀之。州司以闻。上怒,命斩之,怒犹不解,曰:“何物县尉,敢杀吾折冲!”命追至长安面诘之。仁轨曰:“鲁宁对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实忿而杀之。”辞色自若。魏征侍侧,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征曰:“隋末,百姓强而陵官吏,如鲁宁之比是也。”上悦,擢仁轨为栎阳丞。
上将幸同州校猎,仁轨上言:“今秋大稔,民收获者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愿少停銮舆旬日,俟其毕务,则公私俱济。”上赐玺书嘉纳之,寻迁新安令。闰月,乙未,行幸同州;庚戌,还宫。
丙辰,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
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时《戊寅历》以癸亥为朔,宣义郎李淳风表称:“古历分日起于子半,今岁甲子朔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减馀稍多,子初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请更加考定。”众议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风推校精密,请如淳风议,从之。
丁卯,礼官奏请加高祖父母服齐衰五月,嫡子妇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从之。
丙子,百官复表请封禅,诏许之。更命诸儒详定仪注;以太常卿韦挺等为封禅使。
司门员外郎韦元方给给使过所稽缓,给使奏之;上怒,出元方为华阴令。魏征谏曰:“帝王震怒,不可妄发。前为给使,遂夜出敕书,事如军机,谁不惊骇!况宦者之徒,古来难养,轻为言语,易生患害,独行远使,深非事宜,渐不可长,所宜深慎。”上纳其言。
尚书左丞韦悰句司农木橦价贵于民间,奏其隐没。上召大理卿孙伏伽书司农罪。伏伽曰:“司农无罪。”上怪,问其故,对曰:“只为官橦贵,所以私橦贱。向使官橦贱,私橦无由贱矣。但见司农识大体,不知其过也。”上悟,屡称其善;顾谓韦悰曰:“卿识用不逮伏伽远矣。”
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献俘于观德殿。行饮至礼,大酺三日。寻以智盛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上得高昌乐工,以付太常,增九部乐为十部。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宝;将士知之,竞为盗窃,君集不能禁,为有司所劾,诏下君集等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疏,以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讨而克之,不逾旬日,并付大理。虽君集等自挂网罗,恐海内之人疑陛下唯录其过,而遗其功也。臣闻命将出师,主于克敌,苟能克敌,虽贪可赏;若其败绩,虽廉可诛。是以汉之李广利、陈汤,晋之王浚,隋之韩擒虎,皆负罪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赏。由是观之,将帅之臣,廉慎者寡,贪求者众。是以黄石公《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急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伏愿录其微劳,忘其大过,使君集重升朝列,复备驱驰,虽非清贞之臣,犹得贪愚之将,斯则陛下虽屈法而德弥显,君集等虽蒙宥而过更彰矣。”上乃释之。
又有告薛万均私通高昌妇女者,万均不服,内出高昌妇女付大理,与万均对辩,魏征谏曰:“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将军与亡国妇女对辩帷箔之私,实则所得者轻,虚则所失者重。昔秦穆饮盗马之士,楚庄赦绝缨之罪,况陛下道高尧、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释之。
侯君集马病蚛颡,行军总管赵元楷亲以指沾其脓而嗅之,御史劾奏其谄,左迁括州刺史。
高昌之平也,诸将皆即受赏,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以无敕旨,独不受,及别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宝刀及杂彩千段赐之。
癸卯,上猎于樊川;乙巳,还宫。
魏征上疏,以为:“在朝群臣,当枢机之寄者,任之虽重,信之未笃,是以人或自疑,心怀苟且。陛下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上纳之。
上谓侍臣曰:“朕虽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难。”魏征对曰:“臣闻战胜易,守胜难,陛下之及此言,宗庙社稷之福也!”
上闻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数谏争,擢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尝于宫中击鼓,玄素叩阁切谏;太子出其鼓,对玄素毁之。太子久不出见官属,玄素谏曰:“朝廷选俊贤以辅至德,今动经时月,不见宫臣,将何以裨益万一!且宫中唯有妇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听。
玄素少为刑部令史,上尝对朝臣问之曰:“卿在隋何官?”对曰:“县尉。”又问:“未为尉时何官?”对曰:“流外。”又问:“何曹?”玄素耻之,出阁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以为:“君能礼其臣,乃能尽其力。玄素虽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赞皇储,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弃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郁结于怀,何以责其伏节死义乎!”上曰:“朕亦悔此问,卿疏深会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孙伏伽与玄素在隋皆为令史,伏伽或于广坐自陈往事,一无所隐。
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圣,贵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为刺史,独能使其民比屋为善乎!若坐是贬黜,则州县互相掩蔽,纵舍罪人。自今诸州有犯十恶者,勿劾刺史,但令明加纠察,如法施罪,庶以肃清奸恶耳。”
上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征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爪牙;使之执杖,已非后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
言事者多请上亲览表奏,以防壅蔽。上以问魏征,对曰:“斯人不知大体,必使陛下一一亲之,岂惟朝堂,州县之事亦当亲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