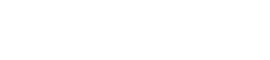第四十二回
铁木金劫道遇官人 为生存长街卖牛肉
上回书说到:铁木金来到北京城,借住在张和家里。这多日子幸亏张和接济,不然早挨饿了。三奶奶说:“你的朋友找不到,难道就光指望接济吗?
过年啦,我不能催你,可你也得想办法,咱们买点儿年货呀。咱们两口子这些日子,也够寒苦的啦,再说,要过个年也得要钱,怎么上人家张大哥的家里去呀,今天都腊月二十八了,你还找不着朋友?”“是呀,这朋友很难找。那么咱们得多少钱哪?”“我算了算,起码你得拿回二十两银子来。”“嗯,二十两?不多。你甭管啦,我,我找去!”铁三爷也没吃什么东西,没的吃啦。伸手到门后把“三顷二十亩”大铁棍抄起来了。“哟,你拿着它干嘛?”
“不,我得拿着点儿棍子,说话就过年了,万一碰上劫道的呢?”“哎呀,劫你什么哪,连个屁都放不响啊。”“这个你甭管!”铁三爷紧了紧裤腰带,打家里出来了。
一个大钱憋倒英雄汉,铁三爷七尺的汉子,到现在一点儿辙都没有了。
举目无亲,二十两银子上哪儿要去?站在这高坡上往南瞧,陆陆续续的打南门进关厢置办年货的人很多。得啦,下坡儿就是大苇塘,置办年货的孤行客,置办年货的都有点儿钱,干脆,我打一号儿闷棍吧!铁木金拉着大铁棍,顺着高坡儿就下去了。溜熘达达往南走,出去有这么几箭地,进了苇塘,抱着大铁棍往苇塘里一蹲,悄悄地往道儿上看。一般从城南来的,都是农村百姓,穿得都不是那么干净,即便腰儿里有几个钱,都是仨一群,俩一伙儿,有说有笑,孤行客碰不上。天又冷,肚里又没食,饿了,煞煞裤腰带,打早晨等到中午,打中午再往下午等,进城的人少了,出城的人多了,十个八个,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又起风了,越来越冷,地冻天寒,干苇子“哗——”直摇。太阳压山了,有点儿云彩起来了,其实天还没黑呢,白天的时光太短了。
猛然间,铁木金听到南边“咣噔咣噔”车轱辘响,原来是辆镖车,车上插着镖旗,上头写着字儿:杭州上天竹街双龙镖局南号小孟长黄灿。只见二十名伙计,一边儿十个,各持刀枪,前头一个报头的骑着小驴,就是当初太湖丢镖的张二。此人大个儿,大嘴岔儿,好嗓音。后头保镖的有两个人,都骑着马,三十多岁,上垂首是灯前少影阮和,下垂首是月下无踪阮璧。一路之上,兼程并进,今天腊月二十九,才进南西门,张二一高兴,在小驴儿上试试嗓子,喊上趟子了。阮和、阮璧在后头说:“二哥,你怎么喊镖趟子?”
“应该喊哪,前边大坟地,苇塘。”“那你要喊出强盗来……”“北京城圈里头,哪儿来的强盗哇?我还没听说过在北京城里头劫镖的呢!只是当初武林之中有位老前辈——浙江绍兴府的飞镖黄三爷,沙滩儿放响马,劫过银橇,那还是成心放份儿,你放心,没事儿!”话音刚落,铁三爷从苇塘里蹦出来了。因为他没劫过道哇,一横大铁棍就觉着自己不得劲,再加上一天了,水米不打牙,眼前头有点儿发黑,脚底下跟踩上棉花一样,“呔!把镖银留下!”
张二一瞧:“嘿!还真出来劫道的了。”阮和一催马,来到镖车前,甩镫离鞍下坐骑。哥儿俩一瞧,嚯!眼前这个大个儿,黑脸儿,五官端正,十分憨厚,攥的这条大铁棍分量可不小。阮和一瞧,有这样儿劫道的吗?就问:“朋友,你劫道啊?”“噢,不全劫。”“你要劫多少?”“纹银二十两,过年就得。”阮和心想:嗨!你要二十两银子多好哇。瞧了瞧铁三爷:“朋友,看来你不是劫道的。”“这个你明白我明白!”“你要二十两银子没关系,你看,我们这镖旗上有字号,我们的分号在大栅栏,你跟着我们的镖车到大栅栏,我们把镖银交了以后,让柜上给你拿二十两,就是百儿八十两都没关系。但你要在镖车头里一横,这可对不起你了,朋友!一分钱你也拿不走,我们得保我们这字号哇。朋友,你跟我们辛苦一趟怎么样?”“不,没那工夫,再说我也饿了,我也走不动了。”“嗨,朋友,你怎么这样儿啊!你劫镖不成啊!”阮璧到底是脾气爆点儿,一摁刀把“呛楞楞”一声响,把刀就亮出来了:“朋友,我哥哥对你说得挺清楚,我们这是有字号的。”铁三爷大吼一声:“劫不出去我要讲打!”铁三爷刚才就觉着头重脚轻,天旋地转,一晃这大铁棍,眼前一发黑,“扑通”,连人带棍倒在地下。阮璧过来,告诉镖师和伙计们:“把他捆起来!”“捆他干什么?”“把他带到镖局问清楚了,真要不是劫道的,给他俩钱儿让他回家。”
猛然间,苇塘以内有人喊:“朋友!等一等!”哥儿俩还以为又出来劫道的呢。阮璧哥儿俩各自摁刀抬着看,“燕子三抄水”“唰——”从苇塘出来一个人,阮和、阮璧一瞧,这位年纪在六十上下,中等身材,猿臂蜂腰,看得出来是个练家。高挽着袖面儿,身上围着亮银链子镢,手里攥着一条硬杆儿大马棒。阮璧问:“这位老兄,您怎么称呼?”这个老头儿托胡子哈哈大笑,一通名姓,敢情是本地西珠汛的五品花翎守备,清真大爸,姓丁,叫丁瑞龙,江湖上称“鼓上飞仙”。丁瑞龙过去是个买卖人,领的是牛街清真寺北边儿路东的一个羊肉馆,叫“北恩利”。东家姓沙,排行在七,所以丁瑞龙领的是沙七爸的东,他在外西华门七圣庙开了一个羊肉铺,代卖馅子货,字号叫“恩顺”。丁瑞龙很能干,柜上用着十几个人,小买卖做得还很磁梆,年年儿都有盈余。北京城这地方做买卖,旧社会讲究赊帐,认得的,知根知底的,到了年下要钱。三十儿晚上,天一黑,拿个折子,在北京叫“溜子”,上边写着住址,人名,短多少肉钱,打着灯笼一家一家要,要到天交五鼓,接神的鞭炮一响,就不要了。所以,大年三十,穷人家有还不起帐的就躲到澡堂子去,接神的炮一响,出来了再见着要帐的说声:“恭喜恭喜,发财发财。”就不提这帐了。当然“恩顺”也不例外,丁瑞龙也去要帐,要了几十两银子,那是大户,可是小户多呀,不但要不了帐,一看人家太难,得了,再借人家三两二两的。等到接神的爆竹响了,这么一看,哎呀,根本对不上帐。跟东家说借给人了,东家不信,说你耍钱输了,要不胡作非为了。丁瑞龙十分为难,不由得走到宣武门外,护城河冻冰了,瑞龙站在那儿发愣,越想越不是滋味儿,顿萌死念。找了块大石头“啪嚓”一下,把很厚的冰凿了个大窟窿。就在这个时候儿,北西护城河的边儿上,树林里头“哗楞楞楞”铁球响,有人挺大的嗓门儿喊:“那不是恩顺家的丁瑞龙丁爷吗?这大年初一的干什么哪?”丁瑞龙一瞧,哟!从树林里出来个大个儿、赤红脸儿的白胡子老头儿,右手托着四个大铁球,铁球晃起来在手指头肚儿上走。再一细看,原来是北京城赫赫有名的铁掌赛昆仑方飞方四爸。方四爸家住在西单牌楼的皮库胡同。
方四爸这个人在北京城露过大脸。有一回,他走在前门大街正赶上下过大雨,道路十分泥泞,有一辆大盐包车误到那儿了,两套儿牲口把式怎么拉也拉不上去,看热闹的人多极了。方四爸一高兴下去了,车把式一瞧:“老爷子您这是怎么啦?”“你把这俩牲口卸喽。我在西单牌楼皮库胡同住,名叫方飞,我给你拉下这车,你这车就上去了。”看热闹的喊好哇!两套车卸了,方四爸一伸右手攥住了辕里头的皮套,单臂一用力,蚕眉倒立,虎目圆睁,把车就给拉上来了。方四爸的这一招“单臂拽盐车”使他成了名了,北京城的人称他“铁掌赛昆仑”。后来有人举荐他在天子的“慎行司”当了内大班的班头。他还有两个盟弟:汤茂隆、何瑞生。当时正赶上康熙皇帝私访“密香居”,在二纽这儿挂着珍奇无比的“十八子伽南秀串”,结果叫一个飞云凶僧给偷走了。方四爸奉命捉拿飞云僧,是后费了很大周折,才把飞云僧拿住了。方四爸心说:得了,我告老了。这样,“慎行司”内大班的班头就归了他的盟弟汤茂隆、何瑞生了。没几年,汤茂隆、何瑞生又交给他们俩的儿子汤英、何玉了。汤英、何玉干了些年,又交给他们俩的儿子了,到汤云、何贵这儿已是三代人了。汤云、何贵,就是拿童林的那两位“慎行司”的班头。方四爷现在到岁数了,在皮库胡同抱着胳膊根儿忍了。虽不说腰缠万贯,但也是吃几辈子吃不了。方四爷每天照样练功,今天初一也一样,老头儿遛早弯儿,其实早发现丁瑞龙了。方四爷一喊,丁瑞龙赶紧过来了:“哎哟喝,老爸爸,我给你拜年吧!”“起来,瑞龙啊,你干什么哪?为什么要寻死啊?”“您要问,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回事,……”一说,然后又道:“帐没收上来,短了东家的钱,人家沙七爸不干,会说我拿这钱不干好事,这可怎么办呢?”方四爷点了点头道:“你呀,说得很有理,你别为难了。”
一伸手把四个大铁球揣到怀里,然后一猫腰,从右边的靴筒里抽出钱夹来了。
那个年头儿,人们搁钱有两个地方,一个叫“靴掖儿”,就是搁到靴筒里头;再一个,“跟头褡裢”里头也可以装钱。方四爷拿出一张三十两银票来,问丁瑞龙:“这是三十两,够不够?”“老爸爸,用不了,过几天我再给你拜年去。”好在是清真老表,没的说呀。给人家方四爸请完安,丁瑞龙回柜了。
来到“恩顺”,今天根本不下板儿,不营业,正月初一呀。丁瑞龙推门儿进去了,见到沙七爸,拜了个年,大家伙儿也彼此拜拜年,说几句吉祥话,拿出银票和折子来,把帐结了。沙七爸问丁瑞龙:“掌柜的,怎么你今儿个晚了,应该接神以前回来?”按理说,瑞龙说句瞎话很自然地就过去啦,无奈瑞龙是个诚实人,就把讨帐反倒借给人家钱,亏了钱,砸冰寻死,碰见方四爷的事都说了。“噢。”沙七爸听完了,只说了声:“好好儿地过年吧。”
丁瑞龙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去了。
到正月初五的晚上,回来了。沙七爸跟丁瑞龙说:“掌柜的,我一个‘北恩利’都忙不过来,所以‘恩顺’的小买卖,我打算明天不干了。大家伙儿哪,我多给几个钱,你也是一样,余外再多给你四十两银子作为花红馈赠。
你呀,打铺盖卷儿回家吧,明天开市以后,另谋高就。”丁瑞龙纳闷儿:买卖这么好,这是为什么?沙七爸有自己的想法,他说:“你跟徒弟师爷一块儿出去要帐,人家全要回来了,你把钱都借出去了。借出去也不是不可以,你为什么要寻死啊?幸亏遇见方四爷,不遇上呢?你扎到河里死了,我大年初一的来条人命,这可怎么办?我决不能再用你了。”瑞龙全明白了:“哈哈哈,好吧,好离好散,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我丁瑞龙没什么能耐,这几年也没给您赚什么钱,但我还年轻,到哪儿耍胳膊,我也能凑合着吃碗饭。”
说完,叫小徒弟把铺盖卷儿打好了,到柜房算了帐,该给自己的拿起来,跟大家伙儿道声辛苦,扛着铺盖卷儿回家了。
回家以后,自己心里不痛快。丁瑞龙心说:沙七爸,这几年我没少给你赚钱哪,你翻脸无情!不用不用吧,明天初六啦,我给方四爷拜个晚年去吧,再说这也有了钱啦。第二天一清早儿,打家里出来,就奔皮库胡同来了。等来到方四爷的家门口,一看人家家里头地方大了,前后得有上百间房子,几层院子,坐北的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两边儿还有门槐,真有份。
丁瑞龙上前去“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个底下人,也就是方家的总管。人家问:“您找谁呀?”“我找方四爷,我给他请安来了。我是恩顺家的掌柜的,叫丁瑞龙。”“噢,您是丁爸,听我们四爷提来着,您跟我来吧。”
方家总管转身形往里走,丁瑞龙赶紧跟上,过了垂花门,一直奔大斤。“唰”一挑毡帘儿进来,丁瑞龙四处观瞧,五间大厅中,四间一通连,靠东边有桦林的隔扇,单有个里间屋,挂着茶青色崭新的门帘儿,隔扇心儿都是名人字画,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均出自名人的手笔。迎面的架几案上,正居中摆着一个羊脂玉的福禄寿三星人,真有一尺多高,“唰唰”地放宝光,底下是紫檀木雕刻得玲珑透剔的座儿,上头有个玻璃罩儿。两边儿是古瓷的帽筒,上垂首有个钧窑瓶,下垂首是个屏镜,迎面的八仙桌,太师椅上的椅披、椅垫、桌围子都是南绣平金的。一人来高的大铜炉子,火苗子“腾腾腾”蹿得很高。
方四爷在椅子这儿坐着,瑞龙赶紧过来请安:“老人家,晚生给您请安了。”
“哎,起来起来。瑞龙啊,怎么今天有工夫?快坐下。”丁瑞龙坐下后,叹气道:“唉,我不在恩顺了。”“啊?为什么?”“沙七爸不用我了。”“你干得挺好的,你也挺有能耐的,怎么辞你啦?”“嗨!就因为初一那天的事儿,我实话实说了。结果他昨天晚上说官话,就不要我了。嗨!我年轻轻儿的,老爸爸,您甭管这事儿了。”方四爷一听火了:“沙七爸这可不对呀,难道你说瞎话就对了?瑞龙啊,你还想再开一个买卖吗?”“老人家,那也不容易,哪儿有那么方便的钱?”“嘿嘿,我前三天下来一笔银子,搁到家里头一点儿用处没有,放到钱铺去,也给不了多少利息,我不乐意。我正想找个人,做个小买卖,养几号人也不错嘛。你看这就巧了,不过我这个买卖,第一,必须是开羊肉馆,代卖馅子活,……”“那我是行家。”“对!第二,必须在七圣庙找门脸儿。”“您瞧,这还真巧了,我们恩顺家对面儿那五间门脸儿,是个绸缎庄关了张的,那房子闲下来了。”“正好了,咱们就一言为定。你先瞧地方去,给我来信盘银子,咱们收拾收拾,立刻就开张,好不好?”“那好,我谢谢您哪,您成全我!”爷儿俩又叙了一阵闲话之后,老头儿同着瑞龙到后头,见着方四奶奶,也拜了年,不在话下。
瑞龙高高兴兴回来了,直接就奔了七圣庙,恩顺家人都看得见。“啪啪”
一叫门,一个看房子的老头儿,把门一拉:“掌柜的,您过年好。您怎么不上那边儿忙去?有工夫上我这儿串门儿来。”“啊!我问问你,你们这房子怎么搁下啦?”“您不知道哇?东伙不和,买卖关了,再说也真不赚钱。”
“你这房了外头写着‘此房招租’哇?”“对呀。”“你们东家……”“我们东家就在北京住啊。”“噢,我知道他,但跟你们东家不常见面儿。我打算租这所房。”“好说,他这房子租不出去,您马上去,给几个钱儿就能租下来。”丁爸出来后可就来到房东家里,跟房东老头儿一见面儿,虽说不熟,也认识,彼此拜个晚年。房东老头请丁瑞龙坐下后问道:“丁掌柜的你有什么事儿呀?”瑞龙把自己的遭遇都说了,最后道:“铁掌赛昆仑方四爸掂着拉我一下儿,让我对着恩顺开个羊肉馆儿。您这房子闲下来了,您说说价码,我认为合适就租下来。”“方四爷都这么仗义,瑞龙呵,我就不能仗义了吗?好吧,给多少钱算多少钱。”结果二位商定之后,丁瑞龙真是没花几个钱,把这房子就租下来了。
丁瑞龙拿着字据找到方四爷说:“房子我租了。”方四爷一瞧,行了,盘出八百两纹银,交给瑞龙了。丁瑞龙再找木工、泥瓦工、油漆工,重新油刷收拾,又按照羊肉馆的门面改了一下,跟着就上家具,商量调货和雇请伙计,一切都非常顺利。丁瑞龙问方四爸:“你给咱们字号起个什么名哪?”
“我早想好啦,你不是为了跟恩顺斗气吗,咱们这字号就叫‘鼎恩顺’,你看好不好?”瑞龙一听:“老爸爸,这对沙七爸不太好吧?咱们叫别的名儿不一样……”“不,就叫这个。这个店就是赌气开的,我就要斗斗这沙七,你甭管,一切全由我做主。他要问起来,你就说我给起的名儿,让他找我来。”
“哎,好吧您哪。”这样找人写字刻匾,把门脸儿收拾齐了,准备择吉日开张。瑞龙里外一忙,有人就告诉沙七爸了:“小伙子跑对面儿开买卖去啦,跟我们对着干。”开张的头天晚上,字号匾用黄纸蒙着,谁都不知道叫什么,方四爷来了,连先生带伙计全叫过来说:“大家多辛苦啊!咱们这买卖要做好了,大家都得益。你们掌柜的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没的说。咱们明天开张,我问问你们,是赚钱的买卖好做,还是赔钱的买卖好做呀?”“老爷子,当然是赔钱的买卖好做呀。”“好!一个月赔一百五十两,先照着二年赔,二年以内不把这些钱给我赔出去,不行。真给我赔出去了,我是加着倍地给。”
哟!今儿方四爷怎么了?老头儿到了岁数了吧?大家伙儿思索不解。
第二天,一亮张,鞭炮一响,一撕匾上这黄纸,“鼎恩顺”三个大金字跃跃欲飞。沙七爸一瞧,气得两眼发直。开张一卖,更了不得了,先生伙计喜气洋洋,您说买哪儿的,人家给您剌哪儿的;您说买一斤,一斤当中多给您个一两二两的,馅子鲜活,肉也鲜活。人们排着队的买。再看恩顺,不行了,买肉的寥若晨星。沙七爸干生气呀!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人家准备一个月赔一百五十两银子。沙七爸说:“咱们不怄气,咱也干不过他方四爸。干脆,关张不干啦!”没仨月,沙七爸说把“恩顺”关了。“恩顺”一关张,“鼎恩顺”这买卖也不那么做了,告诉大家伙儿,多少见个利就得,但是我们一定卖好货,独份儿买卖,更好做啦,老头儿把瑞龙叫到自己的家中:“瑞龙啊,我看你这小孩儿可不错呀。我打算收你做个徒弟,我还有点儿武艺教你,因为你这孩子心里善良。”“哎哟,那我可求之不得,师父!”丁瑞龙马上拜了师。方四爷家里有功房,爷儿俩这二五更的功夫可就搁上了。尽管丁瑞龙的年岁大了一些,但是方四爷有那个份儿,内外两家,双管齐下,瑞龙一边儿照顾买卖,一边儿学武艺。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就是十六年。“鼎恩顺”的买卖扩大了三倍,丁瑞龙的能为也练出来了。
一日,方四爷说:“瑞龙啊,你的功夫不错啦,咱们爷儿俩总算有缘,一晃十六年了,我还认为活不了这么大岁数呢,这都是主的赐福。这样吧,你好好儿照顾买卖,我这儿你就不必再来了。”瑞龙明白师父的意思,哪能不来?每天必来,晨昏定省不缺。过了将近二年。有一天天快黑了,方四爷家里派人来说:“您赶紧瞧瞧去吧,老太太病得很厉害,吃药不见好。”瑞龙赶紧带着伙计来到方宅,一看师母不成了,再请先生瞧,医药枉费,天年已尽,师母无常。按照人家回回的礼节,把师母葬埋了。过了不久,老师病了,病得很轻,是无疾而终。连着两档子大事,全是瑞龙一个人忙的。两件事办完以后,方家没有后代,瑞龙就继承了这一笔财产。这样,瑞龙就搬到皮库胡同师父的家中,然后又把鼎恩顺的买卖安置安置,自己带好了链子双镢,南七北六十三省闯荡江湖去了。
三年的光景,闯出个外号儿,叫“鼓上飞仙”。回来以后,先生伙计们把帐目都交待清楚了,瑞龙说:“甭交待,你们都拿回去,我也用不了这钱,师父这点儿家底儿够我花多少年的。大家伙儿水过地皮湿,都要分些钱。剩下的钱,一,扩大咱们自己的营业;二,南北城有缺与不足,红白事儿什么的,磨脐子压了手揭不开锅,只要借到咱们这儿,无论多少不能驳回。还有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武林豪杰,只要是正门正户,没钱了,提到咱们这儿就给钱。”先生伙计们非常感激丁瑞龙。有人可说了:“您有这么好的能耐,为什么不给老人家倡大门户哇?家里有地方,开个把式场,您教点儿徒弟吧。”
瑞龙一想,这可是个好办法。丁瑞龙就把后门拾掇出来,戳起大杆子教上场了。东西南北城来了几十个,头顶门生帖儿拜师学艺。学生里头有很多有钱的主儿,说:“骡马市有一所房子,我们大家伙儿给您凑上十万两银子,您开个镖局得了。”开始瑞龙不乐意,最后大家劝,没有法子,就在骡马市开了个辅盛镖局。一边儿教学生,一边儿走镖。这一来,丁瑞龙在江湖路上成了了不起的人物。
瑞龙现在六十来岁啦,德高望重,顺天府下了一个委任,任命丁瑞龙这个商人,做西珠汛衙门的守备。这一来,本地面叫瑞龙给维护得虽不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确实少了好些事。眼下正值年关,南西门里南下洼子这一带,苇塘太多,道路狭窄,而且坟地很多,尤其年节,经常出劫道的。丁大爸一想:自己也没什么事儿,干脆这几天经常转着点儿。这样,鼓上飞仙丁瑞龙把链子镢围在身上,半官半民,打衙门里出来,就奔南西门里来了。
每天上午遛到中午,吃点儿饭再来。到了二十九,就发现了铁三爸。看见这个年轻人拿着大铁棍蹲在苇塘里,眼睛瞪得溜圆,紧张地往路上看,丁瑞龙也蹲到苇塘里边监视上他了。可是丁瑞龙纳闷儿:这个人从头至脚,怎么也不像个劫道打闷棍的!等来等去,等到太阳快压山了,天气也凉下来了,镖车来到。瑞龙一看铁三爸动了手,到外头横了镖车,说就劫二十两,丁瑞龙知道他不是劫道的。再看这年轻人还没跟人家动手呢,撒手扔铁棍,“扑通”,就躺下了。阮璧把刀亮出来,说了要捆他,瑞龙高声喝喊:“二位达官!且慢!”丁瑞龙打垫步拧腰出去了。阮和、阮璧赶紧往后撤步,抬头一看:“哎哟喝,朋友。”瑞龙一抱拳:“二位达官,您是杭州的镖啊?”“不错。”
“二位达官怎么称呼?”“我们都是双龙镖局的,在下姓阮,单字名和,这是我的兄弟名叫阮璧。提起我们哥儿俩来,老朋友你可能不知道,但提起我们的授业恩师来,你可能有个耳闻。”“令师是哪一位呀?”“家住山东济南府巢父林侯家庄,姓侯名廷,表字振远。”“哎呀!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圣手昆仑镇东侠侯老侠客爷的高足啊?失敬失敬。”“不敢当。老朋友,您?”
“噢,我是西珠汛的守备,辅盛镖局镖主鼓上飞仙丁瑞龙。”“哎哟喝!原来是丁大爸,久仰您哪!咱们可是同行同道。您瞧,这位劫我们的镖车,还没劫呢就趴下了。”这时候,铁三爸缓过劲儿来了,铁三爸心里难过,长这么大,甭说劫道,从没伸手跟人家要过什么。头一次劫道就碰见守备了,嗨,这也算情屈命不屈。“二位,这件事情你们别管了,就交给我丁瑞龙吧。”
“丁大爷,您多辛苦了,我们哥儿俩可就不管了。不过这位可不像劫道的。”
“这我明白,二位您请吧。”阮和、阮璧回过身来上了马,说了声“再见”,打发镖车奔大栅栏了。
镖车走后,丁瑞龙一伸手搀铁三爸:“朋友起来。”丁大爸细问:“家往哪里?姓氏名字?大腊月二十八的,你怎么跑这儿劫道来了?”铁三爸有些羞愧地说:“您是官人,我犯了国法王章了,情屈命不屈,您带着绳儿了吗?您把我捆上吧。我跟您打这场官司。”铁三爸心想:我饿一天了,您把我带到衙门里头,怎么着也有俩窝头、两块咸菜条儿,哪怕给我点刷锅水喝呢。“嘿嘿,朋友,不错,我是西珠汛的守备,也亲眼看见你在这儿劫道,话虽如此,但我也是出身绿林。你真是劫道的,想不打官司也不成,可我看你不像个劫道的。你跟我说实话。”铁三爸长叹一口气,就把自己的事情由头至尾都说了。丁大爸听完了道:“哎呀,要说你也是膏粱子弟,自己因为好武好练,把家练穷苦了,来到北京城又投亲不遇。张和,噢,我知道,是不是在清真寺南隔壁住的那个张爸呀?”“不错,那位真是个朋友!把房子借给我住,虽说一个月才一百房钱,可是到今天我还没给人家呢,甚至还跟人家借了不少的粮食和钱。我媳妇儿说了,今年过节,没有二十两银子过不去。我媳妇的娘家也是个大财主,无奈我这个人不愿意沾亲戚的光。”“好样儿的!铁三爸,你我都是本教的人,咱们是靠主吃饭的,你的心眼不坏。”
丁大爸看到铁三爸,想起了自己呀!撂下马捧,一伸手从靴掖儿里头拿出一张银票来:“这银票是三十两,你拿着,兑出钱来,买点年货、油盐酱醋的,再割点儿牛羊肉,你们两口子今天过个团圆年。初二,我派人接你搬家,牛街这儿我有房。”铁三爷听完了就呆到这儿啦:“我怎么敢当哪?”“别客气,你的遭遇就是我的遭遇,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你拿着钱票快去吧!天已经晚了,再不去,买不出来东西了。”铁三爸晃晃悠悠地把“三顷二十亩”扛起来,眼泪饶着眼圈儿转哪,看起来哪儿都有好人哪!
上坡儿就是家,来到家门口儿,轻轻地一叫门。三奶奶一听,是丈夫的声音,高兴了,赶紧出去:“哎呀,都把人急死了。”说着话开门,一瞧铁三爸面带笑容,心里踏实多了,忙问:“找着朋友了吗?”“哈哈哈,三奶奶,找着啦!”“哟,这个朋友是干什么的?”“嗨!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哪!咱这朋友,是骡马市辅盛镖局的镖主,鼓上飞仙丁瑞龙,跟我是多年的朋友啦,也是咱们清真老表,他有六十来岁啦,比我大得多呢。给我钱啦,你看看。”铁三爸伸手把银票拿出来了,然后对三奶奶说:“丁大哥说了,让咱们先买点儿年货,今天和明天,咱们两口子在家里过年,哪儿也别去了。初二一清早儿,哥哥就来接咱们,他牛街有房子。”“哎呀!到这个时候儿了才碰见朋友,咱们两口子真得好好儿的谢谢人家。事不宜迟,你赶紧把钱兑出来,买东西吧。”“好嘞!”铁三爸拿着个篮儿,拿着个口袋,打家里出来,让三奶奶把门关好。先到牛街口三合钱铺把银子兑出来,该买的全买了。铁三爸高高兴兴回家了。人得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啊。
铁三爸来到屋中,灯早就点亮了,三奶奶马上刷锅,放水,烧火做饭。两口子这顿饭吃得真香啊。第二天正月初一,也高高兴兴、欢欢喜喜地过去了。
到了初二一清早,两口子老早起来。梳洗已毕,把带来的东西全收拾好了,两口子在家里等着。三奶奶跟三爸商量:“三爸,是不是到张和张大哥家里看看人家去?住人家房子这么多日子了,应该给人几个钱儿了,而且还得谢谢人家呀。”“对!应当还。好在咱们不离开牛街,跟张和大哥住得也很近,这早晚没关系。”正在这个时候,听见外头喊:“铁三爸,起来了吗?”
“哟,这是张和大哥给咱们挑水来了。”两口子一块儿往外走:“大哥!我们正要给您拜年去哪!”“哗啦”一声响,啊?不但张和来了,旁边儿还有一辆车,有个年轻人。张和一抱拳:“兄弟,弟妹,拜年拜年。”“哎呀大哥,我们还没给您拜年去哪,您就来了。这怎么敢当啊?我们正要找您去呢,跟您说点儿事儿……”“我全知道了,丁大爸把我叫到清真寺里去了,把事情都跟我提了,你们的房子就在我家隔壁儿,丁大爸说话就到,咱们先把东西装上车吧。”“大哥呀,我们在您这儿骚扰这么些日子,借您几次粮、几次钱,我们都没还呢……”“没关系,我还告诉您呢,虽说您跟丁大爷交上朋友了,但短与不足,您还上我那儿去,没关系。”“大哥,这可怎么谢您……”
“别谢别谢,哎,咱们赶紧搬东西。”四个人一块儿往外搬。然后张爸把门锁了,把式摇鞭赶车,眨眼之间进了牛街,一直往前走,越走越近,在清真寺南边第三家,紧挨着张和家。几个人把东西全都搬进去,给人家车把式几个酒钱,打发把式走了。张和忙前忙后,帮着铁三爸夫妇两个安好了家。刚收拾完了,院儿里有人说话:“怎么样?铁三爸,家安好了吗?”“哟,丁大爸来了。”两口子挑帘栊,连张和一块儿往外走,把丁大爸接进来了。来到屋中,铁三爸把铁三奶奶拉过来道:“家里的,您给咱们哥哥拜个年吧。”
“丁大哥,我给您拜年。”人家鼓上飞仙丁瑞龙一瞧铁三奶奶,就知道这是个过日子的人。丁大爸对大伙儿说:“张爸、铁三爸,咱们都是回回亲戚,老表一见如故。我当初跟你们夫妻的遭遇一样,我也是要跳护城河自杀,遇见了我的老恩师,我丁瑞龙才有今天。你们夫妻两个碰上我,咱们这就算刀对鞘了,从今以后有个短与不足,张爸你接着,我接二连三地到这儿来看看。”
丁大爸先走了,张爸也就回家了。
这一天,丁大爸来了,三奶奶给烧了点儿茶,老哥儿俩坐下喝茶。“老三哪,你在家里头能干点儿什么哪?”“哥哥,我除了练我这‘三顷二十亩地’以外,别的什么都不会。不然的话,俩哥哥也不至于跟我分了家,我就好练。”“那不行啊,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挣个钱儿啊。”三奶奶说:“要不这样儿,丁大哥,您给我们揽点儿活儿,我可以裁裁剪剪、浆浆洗洗的。”
“弟妹,这不行,这也养不了家。我给兄弟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呀?”
“过两天我给你打辆车子,我那牛肉铺、羊肉铺有的是好牛羊肉,你下街去卖,这还不成吗?”铁三爸心说:行什么,咱们没干过!但看哥哥的意思,我们也不能两口子净吃人家呀。想到这儿,铁三爸说:“哥哥,您给我准备好了,我就试试。”过了几天,推来一辆新车。车轱辘上只是有点儿浮土,铜饰件儿,有个车袢儿,车头里是个钱柜。上头放着割肉的刀,有块大的案板,铺着蓝布单儿,两块半扇牛肉,足有一百多斤,一杆盘子秤。推车来的这位,三十来岁,剃着黢青的头皮儿,一条大辫儿,一身蓝,身上还有个蓝围裙。“您是铁三爸吗?我姓刘,行二,人称刘二爸。我们东家让我把车子带肉给您送来,您瞧缺什么?”“啊,不缺了,我谢谢您了。家里的,把门关上,我卖牛肉去了。”三奶奶出来关街门,说:“早着点儿回来。”铁三爸把围裙系好了,把袢儿往肩上一搭,两只手一架把,一抬身推车走了。刘二爸站在后头,心说:这样人也少有,你倒问问价儿啊?我得跟您说清这是多少肉,本钱多少,卖多少钱一斤,再说也得试试盘子秤啊。等车子走远了,刘二爸在后头慢慢儿地跟着,心说:我先不回柜,瞧瞧您这牛肉怎么卖。铁三爸还推上劲儿了,顺着牛街北口儿出来,可就往东了。刘二爸在后头跟不上,心说:这位是什么意思啊?您卖肉不吆喝?铁三爸推得这快,奔菜市口顺骡马市还往东,到虎坊桥了,他可就拐弯儿了,顺着五道庙进去了。铁三爸生气呀,自语道:“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哪,难道说北京城的老街坊老乡亲连牛肉都舍不得吃吗?怎么没人问哪?”
这时,铁三爸瞧见前面也有一个卖牛肉的车子,人家那牛肉也就剩二三斤了,钱柜里的钱都满了,一看,也是老表。两人走对面儿,老表可就问一声:“掌柜的,上哪儿送肉去呀?”铁三爸答言:“我卖牛肉哪。”“怎么不吆喝呢?”铁三爸张不开嘴,刚要张嘴,对面儿来了个人,咽回去了。一瞧没人了,刚要张嘴,后头有走道儿的声音,脸儿一红,又不敢吆喝了。刘二爸老远的在那看着呢。铁三爸由打五道庙可就奔了李铁拐斜街了。前后没人,铁三爸推着车子,铆足了劲儿喊了嗓子:“好肥的牛肉哟!”真亮的嗓音!整个儿斜街,直到石头胡同北口,都听见了,铁三爸吆喝完了,觉着自己的脑袋都晕了,赶紧推着车子快跑。胡同当间儿有一洼水,有点儿泥浆,一个大门口儿有人喊,“卖肉掌柜的过来,牛肉多少钱哪!”一句话,铁三爸就晕了,哎哟!我也不知道进的价儿,人家都卖多少钱哪?铁三爸愣在那儿了。只听那人说:“朋友,你八成是怕这泥沾了你的车轱辘吧?不要紧嘛,哈哈哈,你把车子端过来。”铁三爸挺拧,心说:我“三顷二十亩地”都练进去了,这三百斤我就端不动啦?冲你这句话,我就端过去!铁三爸的两只手往这车把的根上插,攥着车把的两个四方棱儿,往下一矮身,浑身一叫劲,骨头节儿一响,脑筋一绷,就把这牛肉车子端起来了,晃晃悠悠,又把车子端到路北来了,放到这买肉的眼前头了,铁三爸深深地出了一口气,这才抬头看,买肉的是两人。叫铁三爸端车的是个大个儿,前胸宽背膀厚,虎背熊腰,四方一张大脸,黄白净面,浓眉毛,大眼睛,大鼻子头儿,大嘴岔儿,耷拉着嘴角,让人一瞧好像是撇嘴呢。一身白绵绸裤子汗衫儿,脚底下缎鞋白袜子,喝,好样儿!下垂首这位瘦小枯干,一团精气神儿,穿着一身儿蓝,刀条子一张脸儿,稀稀的眉毛,圆圆的眼睛,小鼻子头儿,三角菱角口,一对锥把子耳朵。两位往那儿一站,看得出来,都是练家子。
其实这两位是姑表兄弟,又是大财主,有上百间的房子。这个大个儿姓石,字叫石勇,号玉山。瘦小枯干的姓冯名昆字永志。石玉山的外号儿叫铁臂熊,冯昆的外号儿叫千里独行。两个人的父母都没有了,万贯家财哥儿俩当家。家里头堂上一呼,阶下百喏。这哥儿俩就是好武好练,但真正练功夫,这两人不行,他们主要是练扔沙布口袋、扔石锁、端沙子筐、拧棒子,披上褡裢摔跤,专练骑拿相横。结交的朋友也都是摔跤的,哥儿俩的跤摔得都不错。今儿早上吃完饭以后,在前边客厅这儿呆着,底下人进来说,“大爷、二爷,你们出去瞧瞧,外头来了位出家的和尚化缘。”“快去,布施十两银子,让人家和尚走。”“我们帐房的先生已跟和尚说了:‘大师傅您要化什么,您说话。’老和尚说了:‘我什么都不化,就化跟你家大爷、二爷见上一面。’”石勇一听,忙问:“此人多大岁数?”“年岁太大了,胡子都白了。”“噢,那我瞧瞧去。”石勇、冯昆两人都出来了,来到大门口儿一瞧,先生伙计站着七八个,老和尚就在台阶儿上站着呢。
老和尚是个大个儿,起码得够八尺左右,双肩抱拢,猿臂蜂腰,由于年岁大了,显着有点儿蚂蜂腰了。赤红脸儿,皱纹堆垒,剃的头皮儿锃亮,明显显三溜九块受戒的香疤,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左眼圆睁,睛芒四射,右眼一道缝儿,一部白胡须苫满前胸。斜插柳背着个大蝇刷,身上穿着灰僧袍,白绫高腰儿袜子。石勇、冯昆两个人一瞧,就知道这和尚很有份儿,赶紧一躬到地:“高僧,您贵上下怎么称呼?”老和尚没提自己的名字,只道:“南无阿弥陀佛,贫僧来到北京城,听说你们哥儿俩在前三门一带颇有威名,老僧不才,前来献丑讨教。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借一步坐,可以吗?”“高僧,请!”两个人马上恭请大和尚往里来,进了大门,过了垂花门,顺着正院儿往东,过箭道往北,过月亮门再往东,进了东跨院儿。北房是五大间,东西房各三间,搭着硬架的天棚,院儿里头,土刨得暄和极了,摔一次跤踩磁实了,用的时候再刨。周围有几条矬脚粗腿大板凳,上头放着几身实纳的褡裢和几条骆驼毛绳。跤场周围,什么礅子、石锁、沙子口袋、沙子筐、檀木棒,全有。石勇拱手相让:“这位大师傅,您请到屋里坐吧。”底下人赶紧挑帘子,老和尚进来坐下,哥儿俩侧坐相陪。老和尚这才细问:“施主,您姓石啊?”“不错。我姓石,叫石勇,这是我的表弟冯昆。”“哈哈哈,老僧讨教讨教可以吗?”“行呵,大师傅,您看得起我们哥儿俩,我们跟您学俩绊儿。您换上褡裢,咱们下场子吧。”“噢,听你们二位这意思,是不是让老僧跟你们摔两跤过过汗儿啊?”“是啊,您不是访我们哥儿俩来的吗?”“老僧的能为不在跤上啊。”“那么高僧您?”“贫僧会点儿武艺,你们哥儿俩情愿奉陪?”“那么好,咱们下场子。”人家老和尚也不撩僧袍,大模大样儿往场子当中一站。冯昆一抱拳:“哥哥,您来我来?”“你先来。”“好吧。”冯昆往前一赶步:“大师傅,在下对不起您了。”说完,左手一晃面门,右手一攥拳,“猛虎出洞”,对准大和尚胸前就是一拳。大和尚没动地方,也没还招,用右手一抬,“澎”!就把冯昆的手腕子给攥住了。左手腕子往起一扬,一扔他的胳膊,冯昆“噔噔噔”来个屁股蹲儿。冯昆脸儿一红道:“哥哥,我跟大师父比差得多,瞧您的吧。”石勇一抱拳:“大师父,我表弟多少差点儿,我跟您讨教讨教。请进招吧。”石勇也往前一赶步,左手晃面门,右手一攥拳,“单风贯耳”,对准大和尚左面太阳穴,右手拳就打来了。大和尚往下一褪头,伸右手“金丝缠腕”一叼,一抖腕子,石勇也来了一个跟头儿。哥儿俩赶紧把大师父请到北屋里头,双膝一跪:“老师傅,我们给您磕头了。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您的弟子,您得教给我们点儿能耐。”
老和尚伸手一拦:“石勇、冯昆,你二人请起。”“老师傅,你得教教我们哥儿俩呀!”“哈哈哈,告诉你们两个,贫僧不愿意做你们的老师呀。”“老人家,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们俩是京城的纨绔子弟,付不下辛苦,受不了罪,没法儿学成。”“老师,您放心,只要老师肯教,我们哥儿俩吃多大的苦,耐多大的劳,也愿意跟您学。”“要是那样儿,除非应老僧三件大事,差一件,老僧不教。”“老师傅,您说吧!”“头一件,练武非一朝一夕之功,如果脑瓜儿一发热、一宠性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朝秦暮楚,这不成。咱们以十年为限,十年以内,除非有了天灾病患,为师认为非歇功不可,才能歇,黑天白日叫什么时候练,就什么时候练。你们办得到吗?”“老师呀,有这么句话:要学惊人艺,须下苦功夫。不付点儿辛苦怎么能把本事学到手哇?这头一件,我们应了。”“嗯,好。第二件,在你们家里找一所比较清净的房子,老僧足不出户。你们把地砸平整了,再买几样儿军刃。十年中,我一分钱不要,但是一年四季的里外僧衣得供我穿。”“这个您放心,怎么着都成。”“好。还有第三件,我收你们为徒之事,不准告诉别人,三亲六故都不准提。就这三件,应了,收下你弟兄;不应,老僧不收哇。”“师傅,这三件事我们都应了,您放心得了。”大和尚这才把武圣人的牌位,达摩老祖的牌位供好,正式收下石勇、冯昆两个人。磕了头以后,石勇问道:“老师呀,您老人家怎么称呼?”大和尚欲言又止,说出一番话来。原来老和尚俗家姓荆,名叫荆立堂,出家的名字叫了然和尚,由于是雌雄眼,又叫一目了然僧。他的师父所收弟兄三个,都是大和尚,他排行在长。二师弟叫通法上人了因僧,三师弟是四川川北拂云峰“极乐禅林”的方丈,叫了义和尚。师弟了义年岁最大,能为最好。荆立堂是河南开封大相国寺的方丈,据说相国寺是战国时期信陵君魏无忌的府第。顺治五年,河南巡抚刘振昌得罪了豫王府的皇粮催头,此人姓李,叫李宽,豫王是他的叔。多铎豫王在河南有很多的庄头,满清一进关,跑马占圈,很多个庄头合在一块儿,由一个催头管。李宽这个催头在豫王跟前说一不二啊!他不出田赋,不交国税,刘巡抚打了他,限期缴纳国税,所以李宽在豫王跟前说了刘振昌的坏话,结果豫王就奏了刘振昌一本,顺治皇帝不察,就革了刘振昌的职。这样一来,激怒了河南黎民百姓的公愤,没有不骂豫王的,没有不骂朝廷的。老和尚荆立堂知道了这件事,心里也很不愤,刘振昌是个好官哪,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不贪污,不吃请,不受贿,不错呀。刘振昌被革职后就住在大相国寺,准备不日进京请罪。这里,老和尚荆立堂先进京了,想给刘振昌报仇。
一目了然僧来到京城,住在广安门里报国寺,挂了单,和大家伙儿一块儿参佛念经。晚上,等僧众们全休息了,老和尚一个人出来,到紫禁城周围,把整个地形都调查清楚了,然后写了一个纸条,上头有八句诗。了然和尚把这个纸条揣好,结果就到了尚宝监,盗出皇上一枚图章来,然后就把纸条儿搁在那儿了。尚宝监的太监名字叫万方和,发现了以后吓坏了,赶紧奏明皇上,把这纸条儿拿上去。顺治皇帝一瞧,上面写的是:“一入皇宫太猖狂,目下河南万民殃,了却僧门不平怨,然后分清红与黄。僧家盗宝无别意,辨别李宽害人常,白奏误准奸王本,冤屈巡抚刘振昌。”顺治看完这字谏以后,勃然大怒,满清刚刚来到中原,民心未附,竟有大胆僧人进入紫禁城盗走国宝,于是便把八大朝臣召进养心殿,字谏掷下,让朝臣们议论,然后马上传旨意,立刻在里九外七皇城四庵观寺院,把所有不明来历的僧众完全都抓起来,严刑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