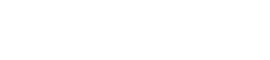蜀山攒黛留晴雪,簝笋蕨芽萦九折。
江风吹巧剪霞绡,花上千枝杜鹃血。
杜鹃飞入岩下丛,夜叫思归山月中。
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
怨魄未归芳草死,江头学种相思子。
树成寄与望乡人,白帝荒城五千里。
赏析
以四句为一绝,这一首诗分为三绝。
第一绝一开头就交代了丝织女工所处的地理环境:“蜀山攒黛留晴雪,簝笋蕨芽萦九折。”
山是密聚的,这些阴森得形成青黑色的大山,不仅像竹笋那样攒簇在一起,而且都高得出奇,以至在这些群峰的顶尖上,闪耀着长年积雪的寒光。若站在这山巅上,还可以看到浮在云端的峨嵋、青城,都不过是和一簇簇的青黛色的蕨芽相似,它们聚在四周,多得如九曲萦回,迤逦得不着边际。诗人一开头就把在这样一个又高又险又无边际的蜀山的形势,以慑人心魄的面貌,推到了读者的眼前。山高险峻,对于游人来说,也许是美的,然而对于远离家乡而又在此受苦受难的弱女子们来说,这就无异是无法逾越的重重封锁。而这也就正是为了拘禁她们而特地选此环境的。以如此险恶的巨大环境,来专门对付这一群弱女子,则她们之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些弱女子,她们禁锢在这里,是绝对不可能再回到她们的耕地上去了。所以,她们所从事这种织丝之手工职业,就不能称之为“副业”,这也就决定她们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基本条件。其实,中国工业的发展,在一开始就带有封建制甚至奴隶制的色彩的。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工人阶级的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少改变。中国工人阶级就是这样走了一千多年的历程。所以直到在中国推翻了帝制,夏衍在写《包身工》时,和温庭筠的这首诗,还是有惊人的相象。
温庭筠不愧是杰出的诗人,他一重山色,几多深情。诗人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直白地说出来,如“满街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那样,虽然明白,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他采用的是现实主义地再现生活的艺术手法,他只是努力地如实写出锦城这个丝织工所生活的典型环境,让读者也一同顺从丝织女工忧伤的眼光去看禁锢她们的大山。这样,他虽什么也没有说,也不因主观感情而去改变客观的真实,他只如实地当然不是自然主义地画出自然。这是因为他相信只要读者理解了丝织女工的感情,也就会读懂他的诗的。因此,要读懂像温庭筠这样的作家的诗词,就一定要设法进入到他为读者设置的特定的感情世界中去,如同诗中的主人公那样设身处地地去读,切不可采取无关疼痒的旁观态度,一看到作品中自然景物的色彩斑斓,就大呼他是唯美主义;一看到他用了“文君”、“相思”之类的字眼,就大惊是什么靡靡之音。他实在是一个最不爱空喊政治口号的作家,读读他的作品,倒不失是对于某些作品的一种纠正。
诗人在让读者对此地环境有了一个轮廓上的概念之后,就把读者的眼光引向有名的锦江,目的是让诗很快进入主题,让读者看到另一批在江边濯锦的工人的劳动。他含着泪,但却是以赞美劳动的声调唱道:“江风吹巧剪霞绡,花上千枝杜鹃血。”
“巧”,当然指的就是所濯之锦了,说明了锦的色泽、花纹,巧夺天工,出奇的美。这是赞美锦,但更是对织锦工人慧心巧手的赞美。江风吹动着这精美的锦,恰似飘动着刚从天上剪下来的彩霞;那上面的花纹,又好像是满山绽开的杜鹃花。从字面上看,写濯锦的劳动和所织出的锦之精美,是非常生动流丽的,诚如苕溪渔隐说的:温庭筠是“工于造语,极为绮靡”的。但绝不能只看到他用词艳丽,就斥之为“无异陈梁宫体”,而要看一看他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例如他的这一联,却是深情地把对工人劳动的高度赞美和对工人命运的深切同情结合在一起来写的。工人的技巧是高超的,成品是精致的,然而命运却是悲惨的。所以他把“花”和“血”有意地联系了起来。锦上的花纹,也许正是蜀地的映山红。而映山红又名杜鹃花,传说此花是由杜鹃鸟的血泪染成的。而杜鹃又是传说中的怨鸟。传说它思乡悲啼,常常泪尽继之以血。这一形象很像集中到这里终身都回不去的女工。这就告诉了人们,这些皇室、豪门、富户们穿的用的艳如霞、美如花的锦缎,正是织女们用年轻的生命和毕生的血泪织成的。这是深刻的揭露。温庭筠当年当然不懂得什么叫阶级,什么叫剥削,然而由于他忠于现实,而且具有同情女工的进步立场,这就使得他能这样深刻地写出了这样鲜明的阶级对立的本质。他这是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要深刻的,因为杜甫仅说出了阶级的对立和不平的悲愤,而“花上千枝杜鹃血”则更道出了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无异于直接告诉了工人:豪门衣上的鲜花,正是用女工们的血泪织成的。这里有巨大的惊心动魄的煽动力量。他是更为深刻地道出了阶级的实质的。这虽不是醒觉者的呼号,但也已是尸林里怨毒之蛇的蜿蜒了。
第二绝承这一思想进一步写女工的悲惨命运:“杜鹃飞入岩下丛,夜叫思归山月中。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
“杜鹃”两句,是花与鸟两种杜鹃的合写,诗人巧妙地从锦上映山红的花纹,过渡到林中啼血的杜鹃。然后借用杜鹃的传说,来暗喻女工们背井离乡,至死也不能回家的愁苦。从花之红,到鸟之血;从怨鸟的啼血哀鸣,自然地引入女工难眠的思绪。则这“夜叫思归”就包蕴了多种含义。
这时如果窗外再传来了杜鹃的那一声声“不如归去”的哀鸣,她们将会十分伤心。可见诗人是非常善于着景设色的。
长夜过去了,尽管一夜不能入睡,可白天还是要照常劳动。濯锦的女工们由于思乡愁苦,神情呆滞,濯锦时只是机械地动着,眼前的流水渐渐地变成了思绪,它波动着,变幻着,于是出现了她的“他”,出现了爸爸妈妈,出现了虽然破落,却满是温馨的家。这“情不尽”是有一千个女子就会有一千种思念的。温庭筠可以说是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懂得运用蒙太奇手法的艺术大师。
濯锦的女工如此,而织锦的女工坐在机子上,思想是不能开岔的。她们只有拚着生命的热力,把青春和心血都织进了锦里,直到她最后倒毙。她们没有作为女人的一切权利,只是老板厂房中的一架机器。元稹《织妇词》说:“东家头白双儿女,为解挑纹嫁不得。”他自己解释说:“予掾荆州,目击贡绫户有终老不嫁之女。”自由民之贡户尚且如此,因卖身而失去了自由的女工就更甚了。这就是诗人说的“文君织得春机红”。这里他用了卓文君的典故,还有另一层意思,因为卓文君最后终于被遗弃,则司马相如当年的那一曲动听的《凤求凰》,也实在是等于欺骗。这和女工招雇的骗局也十分相像。
“文君织得春机红”,“红”,是锦的代指,正如前面已提到的,是杜鹃花之红,也是杜鹃鸟之血。这个“红”,紧紧地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了。它是这样形象地说明了这些被骗来的如“文君”的女子,是怎样把自己青春的颜色和毕生的鲜血换成了锦匹。这里“文君织得春机红”是美的,甚至不妨说它是香艳的。因为文君可以使人想到私奔,而“春”和“红”也可以归于色情一类的字眼。殊不知诗人正是要人们懂得社会是复杂的:它是一个多方面的矛盾总体。他要人们懂得透过封建社会的表面那装饰的美去看到它丑恶的内里的本质,于它那上层的锦团花簇之中去嗅到压榨底层的人民的血腥味。他愿意用这艳丽的蔷薇墨去描绘社会,使它恰如社会之五光十色、复杂多变一样,让人多一些认识和回味到其中的苦乐辛酸,得意和失意的悲伤。文君虽有听琴私奔的罗曼史,但也有受骗、遗弃的伤心史。而诗人在这里,正是把“血”与“红”交替使用的,是把“攒黛”与“荒城”,“春机”和“怨魄”比照着写的。这些女工面临着瘐死穷荒的命运,却织出了一机又一机的如花锦缎,她们在上面用心血编织成了那样些吉祥喜庆的图案,然而她们只是落得别人的快乐逍遥,而自己则精疲力竭地倒毙,最后抛骨荒郊,甚至连个掉泪的人都没有。这些工人比之李绅笔下的那虽“粒粒皆辛苦”,但还是一家团聚的农民,命运更为悲惨。当然,中国工人的前身,就是农民,但他们是无法在农村生活下去的农民。所以写女工的悲惨命运,也就是深刻地写出了中国农村的破落。这是比一般泛泛地写农民的辛苦更具有史的意义与认识的价值的。
最后一绝,声调复从平韵转入了仄韵,而且用的是齿音,使人读来,仿佛听到切齿的恨恨之声:怨魄未归芳草死,江头学种相思子。树成寄与望乡人,白帝荒城五千里。
“怨魄”与“芳草”在这里可以说写的是两代丝织女工,也可说是死生交替的世世代代的丝织女工。诗人为了突出女工们无可逃脱的悲惨命运,采用了层层深入的写法:杜鹃已是死者的冤魂,而且又复化为怨鸟,但还是不能自由地飞得回去,仍然只能是在这里日夜不停地向北哀啼,以至泪尽继之以血;血渍红了草,甚至连草也承受不了它这般的伤心而为之憔悴而死了。这就如“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然而这仍然不能感动那些工厂主,杜鹃还是只能在这里没日没夜地哀啼。死者徒然为怨鸟,怨鸟徒然泣血,血也徒然使得芳草憔悴。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都不能改变这悲惨的命运于万一。写工人之愁苦以及对于造成这愁苦者的怨恨,可以说是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诗人还不肯休止,他又借古时怨女思念丈夫,哭死于树下化为红豆的故事,一方面借此突出女工思念亲人的坚强不屈的精神;另一面,又由此而生发开去,写怨魄的醒觉。意思是说,先前来的工人死了,死后化成的相思树也都已长大了,结子了,经过了如此残酷的现实教训,她们终于懂得了无论是自己怎样的哀号、泣血、变鸟、化树,都不能打动这些公私业主们贪婪的心,因而也就无法摆脱得了自己的这种悲惨的命运。于是她这才对后来的这些像她过去一样,仍在苦苦思归的新工人说:“你们再怎么想也是没有指望的。‘白帝荒城五千里’到了这里,你是一辈子也休想出得去的啊!更何况《唐六典·工部》中早已明文规定了‘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到头来,你们也只能是和我们一样,忧伤地死于他乡,只不过使荒冢延长,去增加此地的荒凉罢了!”
“白帝城”当然不一定专指夔州,只不过是泛指四川而已。而“五千里”也不过是从弱女子眼中看到的逾越之难。从“蜀山攒黛留晴雪”到“白帝荒城五千里”,首尾照应,从青到白,从生到死,可以说是概括了丝织工人一生的心理变化:刚来时看到的是“蜀山攒黛”,犹不失新奇动人;临到死时的感觉,则是“白帝荒城”,寒心于抛骨荒郊,完成了由幻想经现实到破灭、由生经苦难而死的心理全过程,这其中是浸透了悲哀的。因而它俨然是丝织工的一部小史。而且如此深刻动人,以致在一千多年后的《包身工》中,读者还能处处找得到印证。
这里诗人是在揭起这个封建制社会的风花雪月的表面,指给读者以血淋淋的吃人的生活本质。他明确地告诉人们,他写的这样一座攒黛萦青的锦都,其实就是建立在织锦工人的白骨之上的荒城。
诗的结尾看起来是消极的,然而它表现的却是对于统治阶级的绝望。对于统治阶级的绝望,那就应当是被统治阶级觉醒的先声了。由于他深刻地写出了女工们时代的悲哀,也就是深刻地写出了农村破落的悲哀,这也就写出了革命的即将到来。温庭筠所处的时代,正是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唐朝已接近灭亡的时代,这就足以说明他的这种无路可走的感觉,却是深刻的时代的烙印。是以他的这首诗,是可以说“是他时代一定的思想的代表”了。当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时,一场新的革命就要爆发了。温庭筠在诗中虽不能这样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因为他不是一位思想家,然而他凭着一个有着良知的进步的艺术家的敏感,已使他在他的诗中拉满了弓,这种引而未发的架势,也已够咄咄逼人的了。
赏析
此诗当作于唐文宗大和(一作太和)五年(831年)春诗人在成都之时。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词库大全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cnck.net/c658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