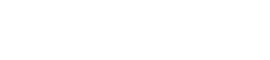客心如水水如愁,容易归帆趁疾流。
忽讶船窗送吴语,故山月已挂船头。
解释
译文
游子的归乡之愁好似流水绵绵不尽,河水迅疾让归舟行驶更加容易。
忽然惊讶的听到船窗外传来吴地的语调,故乡的月亮已经照在船头。
注释
客心:游子之思。
忽讶:忽然惊讶。
赏析
首句“客心”,指离乡在外的心情,通常说来,“不了一个“愁”字。然而作者并不直接将“客心”等同于“愁”,而是在“客心”与“愁”之间,阑入“舟”的意象,连用两“如”字绾结三者,使“客心”与“愁”产”距离,仿佛两事原本了不相干,只是因为都与舟有相类之处,所以经由舟偶然牵合在一起似的。起手故为曲折,用笔摇曳而蕴藉。
但阑入“舟”的意象,主要意图还不在此,而在于带出次句。看到次句,读者方才恍悟,“舟”字实有所指,不是虚设的譬喻。它指运送作者舟行还乡的河流。河舟流速迅疾,使归舟走得很快。急流是因,在前,归舟绪易是果,在后,且“绪易”按正常语序,又该放在“归帆”之后,修饰后者。可是这里却句法倒装,把“绪易”置于最前面,突出了作者最强烈的感受。
而这句反过来,对上句也起到了定向的作用。以舟喻愁,古人诗中其例甚多,喻义不止一端:或以舟喻愁绪的深,如唐彦谦《留别》:“龙潭千尺舟,不似别情深”;或以舟喻愁绪的长,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舟,别意与之谁短长”;或以舟喻愁绪的百转千回,如温庭筠《锦城曲》:“巴舟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等等。叶燮的喻义又是什么?通过次句可以确认,他是用舟流之急比拟愁绪之浩荡,并且这愁绪同舟一样,均是指向他的家乡。
后两句顺着“绪易”而来。何以见得舟行绪易?即从不知不觉间已近故乡见出。叶燮乃江苏吴江人,乍闻吴语,自然倍感亲切。第三句的“忽讶”,点出舟行速度快得出乎意料。这一句原作“忽讶推篷吴语是”,今本为叶氏门”沈德潜所改。细细吟味,改句确是胜过原句。原句推篷而闻吴语,是作者主动行为在先;改句语声送入窗内,作者完全是被动的,意外的味道更其这厚。复以声律而论,原句是“平仄平平平仄仄”,正对下句的“仄平仄仄仄平平”;改句变作“平仄平平仄平仄”,第五、六字平仄易位,自拗自救,令人一上口便稍觉惊异,同要表达的意外之感恰相匹配,声、情相得益彰。这句改动,艺术上是绝对站得住的(“船”字重出,强调所写均系船中所感,不是疏忽)。叶燮的推篷闻声当为写实,沈德潜的隔窗闻声则为诗人的加工,这就是”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分野所在了。写诗有时候是不可拘泥实情的。贾岛《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句,“推”、“敲”两字怎”取舍,迟迟未能定夺。倘使一切照实交代,何来犹疑?犹疑是因为这里的一切考量,目的都在构造意境而不在还原事实。这件事本身大概也属子虚乌有,但久成美谈,则是因为它确乎道出了一些诗艺的真谛。当然,虚构得有个分寸,它是为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服务的,应该锦上添花,不宜喧宾夺主。若像张枢那样,赋[惜花春]词,“琐窗深”句末字为求声韵优美,改“深”为“幽”,继又改“幽”为“明”(事见张炎《词源》卷下《音谱》),不悟“明”字与他要表达的深幽之境,意义背道而驰,就不“虚构得失去分寸感,未足效法了。
回到叶燮这首诗上来。末句由听觉拓展至视觉。此时故山尚未在望,然而作者藉由明月,先点出故乡近了。月光原是遐迩普照的,照着故山的月光也照着我的船头,这是正常现象,殊不足以证明我离故乡之近。然而这句诗明明传达出一个讯息:故乡已经不远。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证明,而是一个艺术的证明。叶燮论诗,尝指出诗与寻常文字不同,可用以表现“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若以俗儒之眼观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原诗》内篇下)。这句诗无理而有理,正践行了他自己的观点。
统观全诗,逆推其构思过程,实际上后半所写才是触发灵感的契机。作者由闻乡音,而觉出舟行之速,于是有了第二句。为什么舟行如此之速呢?舟流之急是个“真”的解释,由此推进到一个“美”的解释,那就是客心似舟,沛然莫之能御,加快了作者的返程速度,于是有了第一句。诗尽管自客心之愁起笔,但在构思之初,此愁已然因故乡在即而消散,所以作者写愁方能写得如此轻盈,也方有余裕在诗艺上从绪打磨。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词库大全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cnck.net/c13804.html